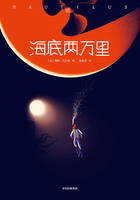
导读 汪洋与孤舟
凡尔纳有多少读者?
法国著名小说家乔治·桑曾专门致信,感谢他的《气球上的五星期》和《地心游记》伴随她挺过了失去爱人芒索的苦痛。
凡尔纳还在世的时候,电影先驱乔治·梅里叶就受其启发拍摄了好几部幻想电影,其中包括1902年那部最著名的《月球游记》。其后,好莱坞和欧洲各国的电影改编不计其数。
到了二十一世纪,他的作品仍然长盛不衰。2005年是凡尔纳逝世100周年,法国政府将它命名为“凡尔纳年”。2012年,凡尔纳的作品被收入伽利马出版社旗下著名的“七星书库”……据2011年的统计,凡尔纳的作品被翻译的次数累计达到4702次,是翻译成外文最多的法国作家。这个纪录,世界范围内也只有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能够超越。尽管如此,凡尔纳在文学界的地位一直是尴尬的,他生前四次冲击象征文学正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宝座,皆铩羽而归,而他的作品长久以来被归入两类“次级”文学:青少年文学和科幻文学,被认为无法登上大雅之堂。如今,凡尔纳曾经着迷的新奇事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寻常;他所竭力描绘的陆地、海洋和天空,普通人就能涉足,或者至少在纪录片里通过高清镜头领略过了。自1900年《八十日环游记》由薛绍徽译成中文,中国读者认识凡尔纳已有一个多世纪。此次大星文化决意重译《海底两万里》,将之列入“作家榜经典文库”,是一个十分和洽的时机,今天我们确有必要再看一看,凡尔纳是怎样的一位作家。
凡尔纳出身于法国南特的律师和船商家庭,自小热爱旅行和历险。中学毕业后,凡尔纳被父亲送去巴黎学习法律。当时正值二月革命,巴黎局势动荡,街头人心惶惶,凡尔纳却在那里找到了人生的志向。他流连于巴黎的文学沙龙,结识了一批文人骚客,如饥似渴地阅读雨果、缪塞、大仲马、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并在学习法律的同时坚持小说和戏剧创作。1851年,他拒绝了父亲安排的工作,在对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文人,但只会是一个差劲的律师。”
就是在巴黎,他结识了雅克·阿拉古。这位传奇的盲人探险家47岁失明,却继续在世界各地旅行,直到64岁去世。他的《盲人回忆录》使凡尔纳注意到了一种当时时兴的创作形式:游记。他意识到,新的科学和地理发现可以结合小说家的生花妙笔和瑰丽想象,勾画出一个绚丽广阔的世界。1863年,在出版了《气球上的五星期》并大获成功之后,凡尔纳和出版商P.J.赫泽尔签订了合同,在之后二十年间为青少年杂志《教育与娱乐》创作小说。而实际上,凡尔纳为这部总称为《奇异旅程——已知和未知的世界》的洋洋大作创作了四十年,包括62部长篇和18篇短篇。《海底两万里》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和最知名的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分两卷正式出版于1869年—1870年,它的诞生离不开上文提到的乔治·桑和1865年她写给凡尔纳的那封信。这位大名鼎鼎的女文豪是赫泽尔的一位朋友,她在信中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还希望凡尔纳尽快创作新的作品,让人物穿上经过他的学识和想象改良过的潜水器材,“带领我们潜入深海”。凡尔纳对于乔治·桑的赏识十分得意,立即就投入到新小说的写作当中。在正式将小说命名为《海底两万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之前,他还曾纠结于《水下旅行》《水下两万里》《水下两万五千里》《大洋之下一万里》等书名之间,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重视,唯恐将这个新奇的题材写砸了。
凡尔纳对科学尤其是地理学有浓厚的兴趣,着迷于最新的科学发现。如果说他的作品充满了文学的诗意,构成其作品的主要元素则来自于学术著作和当时最新的地理、人类学和应用科学的成果。他将游记文学和幻想文学结合起来,并通过可靠的科学知识将其现代化。为此,他查阅了大量资料,是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忠实会员,移居亚眠后常去订阅了大量科学杂志的工业协会图书馆。他长年热衷于各式“高精尖”的科学发明,说他是十九世纪的极客一点都不为过。他的作品大多关注那些当时还未被人类开发的领地:《气球上的五星期》(1863)中的尼罗河源头,《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1864—1865)中的北极,《地心游记》(1864)中的地核,《从地球到月球》(1865)中的月球,《海底两万里》(1869—1870)中的海底世界等等。而他作品中的“高科技”则大多来自对当时最新科学成果的借鉴。《海底两万里》中鹦鹉螺号的原型就来自罗伯特·富尔顿、科埃桑兄弟等人设计的潜水船。好奇的读者可以去巴黎的国立海洋博物馆,那里至今仍保存着一艘曾在1867年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过的潜水船。据说,康塞尔的名字也是来自凡尔纳的一位科学家朋友J.F.康塞尔,此人曾在巴黎的河道里做过潜水船的水下实验。《征服者罗比尔》(1886)中的信天翁号、《蒸汽屋》(1880)中的钢铁巨兽也都有现实的原型。
凡尔纳将新的东西引入了文学写作的范畴,融合了科技、历险和幻想,将科学概念、测量数据、物种和地理名称等奇奇怪怪的东西变成了令人遐想无边的写作元素。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交世界,而凡尔纳呈现的则是一个尚待人类开发的地理和科技的世界。作家朱利安·格拉克说过:“他(凡尔纳)就像哥伦布一样,为文学开拓了一片新的疆域。”这些新的东西来自于他的艺术想象和他所生活的那个充满了变革的工业黄金时代。
凡尔纳是一位进步主义作家,他认为世间的一切,即便最最遥远的地理极致和我们头顶的万尺苍穹,皆会随着科技和认知的发展被人类发现、开发和利用,自然将臣服于人类。1867年,《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前言是这样说的:“《奇异旅程》的目的在于总结现代科学所集合的所有地理、物理和天文知识,并以一种生动鲜活、引人入胜的形式重写宇宙的历史。”“总结”“集合”“所有”“重写”,这些无所不包的词汇表明了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企图!这个写作计划透露着一种十九世纪典型的极权色彩,从文学领域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科学领域的元素周期表,那个时代的人企图将一切置于人类掌握之中,世界将没有秘密,人类将潜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将真相和真理紧紧地攥在手中!
这样的企图是十九世纪的主调,但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却失去了信用。罗兰·巴特曾写过一篇名为《“鹦鹉螺号”与“醉舟”》的短文,将这艘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潜艇和诗人兰波笔下飘摇的小舟作了对比。是的,兰波写于1871年的那篇《醉舟》受到了《海底两万里》的启发,很多迹象可以表明这点,比如该诗第六节的结尾:
从此我漂进了如诗的海面,
静静吮吸着群星的乳汁,
吞噬绿色的地平线;惨白而疯狂的浪尖,
偶尔会漂来一具沉思的浮尸;
《海底两万里》里的读者去看一下小说第二部第一章结尾的乳海和第一部第十八章结尾的沉船和死尸吧!兰波这首诗中对于《海底两万里》的指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巴特眼中两者的区别是巨大的。他认为,凡尔纳建造的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天体起源学”,鹦鹉螺号体现了一种孩童对于树屋或洞穴等封闭空间的幻想。可不是,鹦鹉螺号在十个月间游遍了海底世界,它行驶在异邦的海域,任凭海上浊浪滔天,风雨大作,潜入水下的艇内却保持着欧洲布尔乔亚式的安逸。读者主要可以在第一部的第十一章看到凡尔纳对鹦鹉螺号内部的详尽描写:它的清洁、舒适、现代、有序真是让人觉得凡尔纳把巴黎老爷的理想之家搬到这艘新式潜艇上来了!这大概确实跟凡尔纳本人的喜好有关,他先后购置过三艘游艇,分别叫圣米歇尔I、II、III号。他长期在船上办公,甚至《海底两万里》的上部就是在英国航行期间完成的。
凡尔纳对完满有着一种迷恋:他不断地想要穷尽这个世界,装点它,将它像鸡蛋那样填满;他的行为和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作家和荷兰画派的画家别无二致:世界已经被完成了,充满了可以一一列举的连绵不绝的物品。艺术家所要做的就是编制目录和清单,搜寻那些空白的角落,用人类的造物和器具将它紧紧地塞满。
巴特眼中的凡尔纳是无聊的。数落完凡尔纳,他最后说道,在所有的文学创作中,大约只有兰波的醉舟才是鹦鹉螺号的反面,因为它消解了人这个主体,只剩下以“我”自称的醉舟随波逐流。
巴特在这则短文中以寥寥数言一抑一扬,将凡尔纳说成了他所痛恨的小资产阶级安逸的代表,以此衬托了兰波狄奥尼索斯式的诗意。在巴特看来,凡尔纳展现的是人类对世界的占有和同化。作为凡尔纳神话学中的重要形象,船是居所的延伸和变体,精工打造的鹦鹉螺号更是其中的代表,它使得主人公可以像踩在坚实的大陆上那样,不费什么力气,就展开对大海的探索。然而,倘若凡尔纳真的如此无味,又怎能激发倨傲的少年诗人写下如此潇洒的诗篇呢?巴特的文艺批评涉猎广阔,精彩非凡自不用说,但他对于凡尔纳的评判却未免过于绝对。
相比之下,朱利安·格拉克的看法就少了许多偏激 。他在凡尔纳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过渡。他认为,凡尔纳处于一个起承转合的位置;诚然,他对于封闭的场所有着一种迷恋,但有的时候,比如在《神秘岛》中,这个巨大的封闭岛屿上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还认为,凡尔纳敏感地意识到,人类正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速度和移动的时代。
。他在凡尔纳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过渡。他认为,凡尔纳处于一个起承转合的位置;诚然,他对于封闭的场所有着一种迷恋,但有的时候,比如在《神秘岛》中,这个巨大的封闭岛屿上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还认为,凡尔纳敏感地意识到,人类正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速度和移动的时代。
孰是孰非,我们还是看看作品吧。《海底两万里》和《奇异旅程》中的其他故事一样,反映出十九世纪的重大主题:国家间的战争、殖民主义、民族独立运动、资本主义上升和人类命运的走向等等。尼莫船长亦正亦邪,折射出科学和文明的双面性。这位从欧洲的科学和艺术殿堂中汲取了一身本领的印度王子 对博物学家阿罗纳克斯失望地说道:“人世已经完结”,“人类再没有什么思想”。他可以是拯救弱者的英雄、无所不知的学者和无所不会的工程师,也可以是失去心智的毁灭者。这位饱受精神折磨、把自己叫作“无有之人(Nemo)”的主人公不正是开始自我怀疑的理性主体的化身吗?他和船上其他无差别民族的放逐者们永远地放弃了陆地,将大海视为第二故乡,使得鹦鹉螺号这艘在大海里自给自足的潜艇成为一座乌托邦。而小说末尾的疯狂和杀戮又流露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情绪。凡尔纳晚期的作品则更加黑暗,比如《征服者罗比尔》或《旋转乾坤》(1889)中,科学造就了可怕的魔鬼,或者说,人类变成了可怕的魔鬼,几乎将世界毁于一旦。凡尔纳的这些小说体现出对工业社会的悲观思考。
对博物学家阿罗纳克斯失望地说道:“人世已经完结”,“人类再没有什么思想”。他可以是拯救弱者的英雄、无所不知的学者和无所不会的工程师,也可以是失去心智的毁灭者。这位饱受精神折磨、把自己叫作“无有之人(Nemo)”的主人公不正是开始自我怀疑的理性主体的化身吗?他和船上其他无差别民族的放逐者们永远地放弃了陆地,将大海视为第二故乡,使得鹦鹉螺号这艘在大海里自给自足的潜艇成为一座乌托邦。而小说末尾的疯狂和杀戮又流露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情绪。凡尔纳晚期的作品则更加黑暗,比如《征服者罗比尔》或《旋转乾坤》(1889)中,科学造就了可怕的魔鬼,或者说,人类变成了可怕的魔鬼,几乎将世界毁于一旦。凡尔纳的这些小说体现出对工业社会的悲观思考。
另外,我们也不要忘记,凡尔纳除了喜爱雨果、大仲马、缪塞、莫里哀、莎士比亚和莫泊桑,更是爱伦·坡的狂热拥趸。他通过波德莱尔的译笔发现了爱伦·坡,并为这位钟爱的作家贡献过一生中唯一的一篇文学研究:1864年发表在《家庭博览》杂志上的《埃德加·爱伦·坡和他的作品》。凡尔纳不仅在《海底两万里》中屡次提到坡和他的《亚瑟·戈顿·皮姆历险记》,甚至还为该书撰写了续篇《极地斯芬克斯》(1897)。也许是受到这位“诡异大师”的影响,在表面的理性之间,怪异和奇幻这些属于非理性范畴的东西在凡尔纳的笔下滋长,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想象,就以《海底两万里》为例,血腥的鲸鱼大战、可怖的巨型章鱼、诡谲的大漩涡,乃至南极的冰雪世界都有一种静寂幽怖的神话色彩。
是的,凡尔纳的身上有一种两面性、暧昧性,或者格拉克所说的过渡性。他一方面在颂扬着主体和理性,一方面又怀疑着,深深地惊异于这个不断扩大的新世界对于人类来说的异质性和不可同化性。凡尔纳的想象力创造了那些今天已经过时的机器,但他所创造的那个神话世界却是与所有人类息息相关的。这个神话世界披着现代的外衣,却是和荷马的神话、圣经的神话相通的,它是一首十九世纪的奥德赛,是人类关于自身身份和命运的终极问题的回应。凡尔纳的两面性是他代表他的那个时代给出的回答,而他的回答也为后世的回答投去了一道曙光。
如今,我们已经目睹了自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思想铸就的世界的稳定性是如何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逐渐分崩离析的,而当今的科幻电影,从《2001:太空漫游》到《异形》,尤其体现出这种人类意识深处对于熟悉和陌生、占有与失控之间的恐惧和焦虑。从这一点上看,正像法国学者让·贝西埃等人在1988年就指出的那样,凡尔纳的身上体现出一种现代性 。
。
也许,他是一个文学史教材里不大会提及的作家,但阅读凡尔纳,不断地让我想起,千百年来,我们永远都是颠簸在汪洋上的鹦鹉螺号,无所不能,却注定漂泊。

2018年5月28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