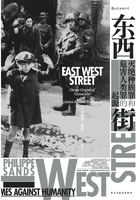
34
短短几年,劳特派特在伦敦已经有了归属感,远离了中欧的持续骚乱。他和拉谢尔住在克里克伍德沃尔姆巷103号的一所小房子里,位于伦敦西北绿树成荫的城郊,离我家不远。在参观的时候,我注意到入口的瓷砖已经不见了,但正门周围的木质装饰仍然保留着,现在被漆成绿色。如果劳特派特偶尔手头紧缺,麦克奈尔会借一小笔钱帮助他。
1928年夏天他很忙碌,去华沙参加了国际法协会的会议,这次是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他从那里前往利沃夫探望家人。他的哥哥达维德和法律系学生宁希雅结婚了,有了一个年幼的女儿埃丽卡。他的妹妹萨宾娜也结婚了,丈夫是马塞尔·格尔巴德(他们唯一的孩子,一个名叫因卡的女孩,在两年后的1930年出生)。这次出差,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他流利的波兰语令初次见面的人大感意外,那是他儿时在若乌凯夫和伦贝格的第一语言。波兰司法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询问他为什么能说一口“这么好的波兰语”,他讽刺地回应道:“多亏了你们的名额限制。”(指的是利沃夫阻止犹太学生学习深造的规定。)
当时劳特派特在麦克奈尔的指导下获得了第三个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国际法的私法渊源和类比》61,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却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论文追溯了国家法规对于国际法发展的影响,探寻两个法律体系之间的桥梁,并希望借此填补国际法规的空白。凯尔森对宪政审查权力的信念继续影响着他,也许同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也影响着他,向他揭示了个体的重要性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劳特派特将继续这一主题,在众多选题中着重于这一个。
推进他研究工作的一大要素是,作为《凡尔赛和约》产物的首个全球法庭创立了。常设国际法院设在海牙,于1922年开始运行,致力于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在它所适用的国际法渊源当中——主要是条约和习惯法——包括了“文明国家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这些可以在国家法律制度中找到,因此国际法的内容能够借鉴已经较为完善的国家法律规则。劳特派特认识到,国家法和国际法之间的这种联系为制定规则提供了“革命性”的可能性,从而对国家所谓的“永恒的、不可剥夺的”权力施加更多的限制。
出于务实和本能,劳特派特坚信控制国家权力是可能的,这是伦贝格的生活和法律课程教给他的。要达成这个目标,不是靠作家或和平主义者的许愿,而要靠严谨、有根基的思想,通过实现公正,为“国际进步”62做出贡献。为此,他希望建立一个不那么孤立、精锐,对“外部影响”更加开放的国际法体系。他的博士论文《用国家法律的一般原则来加强国际义务》 于1927年5月出版,获得了大量学术赞誉。直到今天,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仍然被看作是为国际法奠定基础的著作。
这本书为他带来了更广泛的认可,并于1928年9月使他得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助理讲师的工作。麦克奈尔认为他在选择国家时很幸运。“我认为除了在体育比赛和股票交易的场合,英国没有多少对外国人个体的敌对情绪,”他解释说,“可能过于乐观,即使在议会和新闻媒体上的确有‘不少排外情绪’。”麦克奈尔认为,劳特派特选择在英国生活“是我们的福气”63。尽管如此,麦克奈尔还是会嘲笑他欧洲大陆式的高傲。“为什么要用‘常态’这个词,”他问,“对于庸俗的英国人来说,太‘文绉绉’了。”务实的麦克奈尔鼓励劳特派特成为大律师,融入伦敦的法律界,进入这个圈子。劳特派特做到了,但是止于某一点(1954年,作为国际法院英国法官的候选人,劳特派特遭到反对,结果失败了,国会议员总检察长莱昂内尔·希尔德爵士反对的理由是,在海牙法庭上英国的“代言人”应当“从内到外都是彻彻底底的英国人,而劳特派特无力更改他的出身、名字和教育背景皆不符合资格的事实”64)。
麦克奈尔把他的门徒定性为一个完全没有“一丝一毫政治煽动者气质”的人,然而却“渴望实现正义”65和“解除痛苦”。麦克奈尔认为,他从1914年到1922年在伦贝格和维也纳所经历的事件促使他将保护人权作为“至关重要”的信念。个体应该“拥有国际权利”,从很多方面来看,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这都是一个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想法。
如果说劳特派特想念利沃夫,那也是想念家人,而不是那个地方。他母亲的来信甚至加重了他的忧虑,信中写道,“现在家里不太好”66,指的是经济上的困难。1928年,她第一次到伦敦去看望那年新添的孙子伊莱休。儿子欢迎她的到来,但批评了他母亲的个性表达,强烈反对她“染指甲”67,迫使她除去指甲油。
他同样反对他的母亲对拉谢尔的影响,劳特派特看到她梳着路易斯·布鲁克斯式童花头的新发型时,直呼“刺眼”,并坚持要她改梳回圆发髻。继而引发了这对夫妻的一次大争吵,拉谢尔威胁说要离开他。“我有权而且必须不受你欺压地过我无害的私人生活。”68可是最后,拉谢尔还是让步了:50多年后,当我见到她时,她依然梳着圆发髻。
个体权利属于一部分人,但不包括他的母亲和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