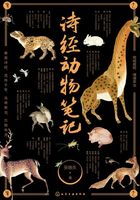
豺:超越狼群,轻松联合起来战斗

很多年前父亲告诉我,豺比狼还聪明,它们捕猎的时候,善于掏猎物肛门,然后将整个肠子拽出来,猎物跑着跑着肚子就空了,倒下。这一点给我留下终生印象,现在说到豺都觉得“菊花”一紧。
其实豺快玩完了。有资料说野生豺在地球上不足5000只,在我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现在谈豺,只能对着照片寻找微弱的现场感。
我童年居住的地方,离合肥紫蓬山不远。在我父亲的童年时代,那里是真有豺、狼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个夏夜,附近村里有孩子乘凉失踪,第二天才在田野草丛找到他的一只鞋。大人说,是被豺或狼衔走了。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
取彼谮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小雅·巷伯》)

自古就没人把豺当作好东西。《巷伯》里的豺是阴险小人的代称。那时的荒野,豺神出鬼没,通常都在清晨和黄昏,其捕猎方式可能给我祖先以深刻印象——谁不愁“菊花问题”呢?那种可怕的痛苦,绝非痔疮可比!
这种凶猛的野兽,外貌介于狼与狐之间,毛色偏红。据说安徽皖南山区还能偶尔见到野生的豺。不过,因为不成气候,对人的威胁倒不大。
一旦有成群的豺,其杀伤力比虎、狼还厉害。资料记载,豺在饿的时候,虎口夺食的事都敢干,而老虎最终落荒而逃。因为一群豺会联合起来,从各个方面扰乱老虎,使它疲于应付,最终智商与体力全面下降,不得不主动滚下擂台。
宋代诗人贺铸《和邠老郎官湖怀古五首·其一》有道——
白也遭时网,临年放夜郎。
何妨去物远,当道横豺狼。
——其实豺与绝大多数猛兽一样,并不喜欢直接与人作对,为何古人非得如此贬低它呢?如果我们观察人性,会发现,怕与恨是紧密相连的。一个人手里拿把刀,面前出现一只白兔和一匹狼,那么手里这把刀会对着谁呢?怕谁就对着谁——狼——而非白兔。

怕直接产生恨。祖先可能偶尔受到豺这种高智商野兽的侵袭,比如大雪季节食物匮乏,豺群说不定也会像鬼子进村一样无恶不作。所以,古典文学中豺的意象,就一路毁下去,没有翻身机会。安史之乱的时候,李白心情不好,有一天好似做梦一样,登华山莲花峰游玩,遇见几位神仙,乘坐仙禽飞翔到洛阳上空——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又是一次对人间“豺狼当道”的哀叹。这真正的豺也实在委屈:俺们不过偶尔祸害人,与人祸害人相比,俺们很单纯很善良哦!
是的,豺的单纯,导致其团结精神比人类更强。“乌合之众”永远不能针对豺。这一点它们甚至超越狼群,因为即便不同种群的豺,都能在同一个目标感召下,当即联合起来战斗!而且是轻轻松松联合起来战斗!
单个的豺也不可小觑,它的单兵作战能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莫斯科有过惊人展示。当时的动物园引进一对青海豺,露天圈养,外面有4米多宽的壕沟,沟外是1.2米高石墙,再外围还有1.5米高铁丝网。结果“那只雄豺一跃而出,到莫斯科繁华大街上游览一番”!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合肥逍遥津动物园里养过豺。但它颠覆了父亲为我塑造的可怕形象。
它们住的“牢房”很小,条件比乡村猪圈稍好。老远就能闻到骚臭气。
我记得豺在“牢房”里转圈跑步的姿势,非常灵活,不时停下来与我对视,然后再转圈跑。那神态并无焦急,似乎在玩。它的眼神我至今还有印象:有点深邃,似看非看。你不能通过豺的眼神,去揣摩它的内心。
一只笼子里的豺,比不了一只野狗。有关豺善于“掏菊花”的传说,怎么也和它联系不起来。
近年的四川黑水河自然保护区因为人类活动减少,又出现豺了,总共十来只。据说它们为当地消灭许多害兽,如野猪、獾子,使得农民们尊称其为“神豺”。这是我翻阅资料时看到关于豺的唯一的正面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