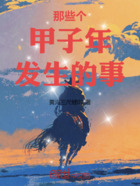
第549章 公元前57年之大汉王朝(二十)
汉宣帝刘询深知郡太守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他坦然指出,郡太守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堪称“吏民之本”。
在他看来,郡太守的职位如果频繁调动、变易无常,
就会导致他们无法赢得属下的尊重,上下之间也难以实现和谐共处。
相反,如果实行“久任”制度,百姓知晓郡太守将长期在职,
自然不敢欺瞒上司,从而“服从其教化”,地方治理也会更加有序。
为了激励郡太守积极治理地方,宣帝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奖励机制。
对于那些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他常用的奖励办法包括:
颁布玺书公开嘉奖勉励;在原有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
赏赐一定数量的金钱;
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其既能享受政治名誉,又能获得经济利益。
例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成功安抚了大量流民,政绩“治有异等”。
因此,他得到了宣帝的明诏褒奖,其俸禄被提升为“中二千石”,并被赐爵关内侯。
另一位名臣黄霸,曾因过失被贬,后来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
他在任八年,使颍川郡大治。
宣帝下诏称扬他的政绩,并给予“赐爵关内侯,
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
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
尽管他们的职务没有升迁,但他们的政绩得到了肯定,
待遇得以改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
这种奖励方式不仅对当事人起到了安抚和激励的作用,
还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从而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
这些循吏或良吏在治理地方时,执法公平,
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
他们所治理的地方百姓富足,他们离开的地方也常被百姓感恩戴德。
因此,他们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
史书上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这表明在宣帝时期,良吏辈出,
地方治理成效显著,国家也因此迎来了中兴的局面。
汉宣帝刘询出身于民间,深知百姓对官员贪腐的切齿痛恨。
因此,他一当政,就主张严明执法,坚决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
在他的治理下,一些地位极高、腐朽贪污的官员纷纷被诛杀,彰显了他整顿吏治的决心。
其中,大司农田延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田延年在尊立宣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
然而,他在修建汉昭帝平陵时,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高达3000万钱。
此事被丞相议奏,田延年被定为“不道”罪。
宣帝得知后,要求用自己的私钱——水衡钱来为昭帝修建平陵,以示公私分明。
几天后,使者前来召田延年到廷尉处听罪。
田延年深知罪责难逃,最终选择了自杀。
宣帝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宽政闻名。
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一方面,启用了一批精明能干的能吏,严厉镇压不法豪强;
另一方面,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
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于宣帝自己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他对冤狱深恶痛绝,
决心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
亲政后不久,他便亲自参与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以确保司法的公正。
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公元前67年,宣帝在朝廷增设了四名廷尉平一官,
专门负责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
以审核廷尉量刑的轻重,防止司法不公。
公元前66年,宣帝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
这一举措大大减轻了百姓的法律负担,
避免了因一人犯罪而牵连无辜的情况。
他还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鼓励百姓畅所欲言,为国家建言献策。
公元前54年,宣帝派遣24名使者到全国各地巡查,
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
此外,他还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释放了许多因冤假错案而被囚禁的百姓,
进一步彰显了他宽政爱民的治理理念。
宣帝的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打击了贪腐,
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还通过宽政安抚了百姓,缓和了社会矛盾。
他的治理方式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
又彰显了人性的温度,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元帝刘奭为太子时,性格柔仁,崇尚儒学,
对宣帝时期的治国方针颇有微词。
他见宣帝任用的多为精通法律、善于以刑名之术约束臣下的文法吏,
且大臣如杨恽、盖宽饶等人因言辞讥讽朝政而被诛杀,心中颇为不安。
一次,元帝在侍奉宣帝宴饮时,委婉地劝谏道: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他认为,朝廷应当更多地任用儒生,
推行德教,以仁政治国,而非过于依赖严刑峻法。
宣帝闻言,脸色骤变,严肃地回应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他明确指出,汉朝的治国之道是“霸王道杂之”,
即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仁政德教相结合,而非单纯依赖儒家的德教。
宣帝进一步批评儒生,
认为他们“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在他看来,儒生往往拘泥于古代的理想化政治,
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容易导致名实混淆,使国家治理陷入混乱。
宣帝的这番话不仅是对元帝的训诫,也是对汉朝治国方针的深刻总结。
他深知,单纯依赖儒家的德教或法家的刑名之术,都无法应对复杂的现实政治。
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宣帝的治国理念,正是对汉武帝时期确立的“霸王道杂之”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这一制度强调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既注重法律的严格执行,
又提倡儒家的仁政教化,从而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注重民心的凝聚。
宣帝对元帝的劝谏并不满意,甚至感叹道:
“乱我家者,太子也!”
他预见到元帝过于崇尚儒学的倾向,
可能会偏离“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
从而导致国家治理的混乱。
这一预言在元帝即位后得到了验证。
元帝重用儒生,推行纯任德教的政策,导致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吏治松弛,豪强势力抬头,最终为西汉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汉书》中的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材料。
从汉武帝时期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到宣帝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再到元帝时期的偏离与衰落,
这一制度的演变反映了汉代政治思想的变迁。
宣帝一语道出了“霸王道杂之”的要诀,
即法治与德治的结合,这一制度在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借鉴了“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
无论是唐朝的“贞观之治”,还是明朝的“洪武之治”,
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以强化其统治。
这一制度的历史意义,
不仅在于它为汉朝的繁荣与稳定提供了保障,
更在于它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