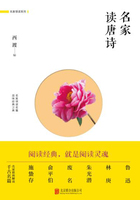
第5章 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襄州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人。曾隐居鹿门山。年四十,赴长安应进士举,失意而归。张九龄镇荆州时,被张招致幕府,后病疽死。
他一方面自居隐逸,另一方面又不无盛世沉沦之感。其诗多写山水闲情和羁旅愁思。用清微淡远的笔意,表现狷介郁抑的情怀。佳处在于伫兴造思,出入幽微,不落凡近,略无雕琢藻绘的痕迹,故能在盛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与王维并称。
有《孟浩然集》,共诗二百余首,绝大部分都是五言短篇。
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释孟浩然《春晓》【1】
周振甫
唐朝著名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是唐诗中传诵的诗篇之一。这首诗,《唐诗三百首》里选了。蘅塘退士孙洙讲他选《唐诗三百首》的标准说:“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那么在孙洙选诗时,这首诗就已经成为脍炙人口之作了。
这首诗写诗人在春天破晓时,还迷糊睡着,没有感觉到天已发亮。但在迷糊中听见到处的鸟叫声,醒来想到夜里的风雨声,不知道花落掉多少。从这里,可以体会到诗人夜里听到风雨声,为花担心,睡不着觉。后来风雨声停了,诗人才朦胧睡去,所以天破晓时还在迷糊睡着。但在迷糊中还在关心花事,所以能够听到到处的鸟叫声,知道天已放晴。这是从诗里可以体会到的。
《文心雕龙·知音》里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诗人写这首诗,是情动而辞发;我们读这首诗,是披文以入情。那要“沿波讨源”,这里还有“世远”的时间距离,要缩短这种时间距离,才能够“辄见其心”,了解诗人的情意。
先就“世远”讲,怎讲缩短时间距离呢?光从《春晓》一首诗里去了解诗人的心情,可能有困难,那可以用诗人别的诗来印证,或从诗人同时代人的诗里去印证,了解诗人同当时人看到花落时的心情。早于孟浩然的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陈子昂的《感遇》诗:“但恨红芳歇,凋伤感所思。”诗人对“花落知多少”的关心,是不是也有像刘希夷、陈子昂那种看到花落引起青春易逝的感叹呢?诗人在《晚春卧病寄张八》里说:“狭径花将尽,闲庭竹扫净。翠羽戏兰苕,赤鳞动荷柄。念我平生好,江乡远从政。”他把花落同竹净和翠羽赤鳞连起来写,即把花落同美好景物连起来写的,并没有因“花将尽”而引起春光易逝的感叹。他的感叹是从怀念“平生好”里引出来的。再从别的诗里,也找不到他看到花落而引起春光易逝的感叹。那么要从《春晓》里探索诗人的心情,从诗人的诗集里找不到刘希夷、陈子昂那样借花落来抒怀的诗,那就不能用花落抒怀那样的写法来探索诗人写《春晓》时的心情,得结合诗人别的诗来探索诗人的心情了。
王士源序孟浩然诗称:“每有制作,伫兴而就。”什么叫“伫兴”呢?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伫兴类》称:“萧子显云:‘登高极目,临水送归;早雁初莺,花开叶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也就是情以物兴,有所感触。王士禛又在《真诀类》称这种感触为兴会,比作“镜中之像,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上面想从《春晓》诗里探索它的用意,有没有青春易逝的感慨,这就是求迹象,可是这种伫兴之作是无迹可求的,所以上面的想法就没有抓住孟浩然这首伫兴诗的特点。胡震亨《唐音癸签·评汇》称“萧悫有‘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孟则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谢朓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与古人争胜毫厘”。芙蓉一联,《唐才子传》称他与诸名士集秘书省联句所作,为众所钦服。这些诗,描绘景物,写出一种境界,即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的“无我之境”。无我之境并不是完全无我,如王国维讲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但在“悠然”和“采菊”里就有我在。不过在这里,陶渊明没有在诗里着上强烈的感情色彩。那么《春晓》诗的好处,就在于伫兴而作,写出一种无我之境来,它不以命意取胜,是以写出一种境界来,表达了诗人的兴会。这种兴会,正像花开叶落,有来斯应,有这种感兴,却说不上有什么寄托。
诗人听见处处鸟叫,引起关心,喜欢天气放晴,这是伫兴。诗人听见风雨声,引起关心,关心花落,这是伫兴。这种兴会,即从接触外界的晴或风雨来的。他没有从中引出更多的思想来,像刘希夷、陈子昂那样。他的情意就停留在情以物兴上,并不从关心花转到关心人,从花落感叹身世飘零,那样成了感怀,借花落来写人,主要在写人的身世飘零,不在写花落,那就不是伫兴了。伫兴是情停留在物上,如绘画,画出风雨落花图,究竟画家面对这幅画有什么含义,没有说,就让人去欣赏这一幅画面。由于没有从花落引出身世飘零来,只写花落,所以是无我之境。
这种伫兴之作,以画面取胜,从画面中写出一种境界来。诗情就表现在画意里,诗人的心情在画意中透露出来。《唐音癸签》里又称引:“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净,真彩自复内映。”这几句说明孟浩然诗的特点,《春晓》诗也是这样。气象清远,出语洒落,洗脱凡近,它不同于一般的写风雨落花诗,确实做到浑然省净,语极简练干净,浑然天成。他只描绘自己感觉,没有多余的话,不写什么意义或感受。它的另一特点,是不依靠辞藻,是“真彩自复内映”。它的彩色是真彩,不是靠涂饰加上的,是自然形成的;是内映,是从内部映发出来的。从《春晓》看,不用辞藻,语言是朴素的。但在朴素的语言中自然具有一种真彩。这种真彩,只要把全诗构成意境展现在我们眼前,就可想象到一种画面,有风雨落花,有处处鸟鸣的晴晓,这里就给人一种彩色的感觉,这就是这首诗所具有的真彩。
这样看来,《春晓》的好处,像上面指出的,诗人关心花而高兴天晴,关心花落而夜不成寐,这些是言外之意,没有说出,可以从说出的话中体会的。这是一。《春晓》写无我之境,有画意,是伫兴之作。诗人的诗情就从画意中透露出来,写出一种境界。这是二。《春晓》出语洒脱,不用刻画,浑然天成,语言自然省净。这是三。《春晓》不用词藻典故,从画意的含蕴中,自然含有色彩,是真彩内映。这是四。这首诗是不是含有这四种好处,具有诗人伫兴之作的特色。这样看,是不是做到了“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觇文辄见其心”呢?这些,是不是使这首诗成为传诵之作呢?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1],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2],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3]。
注释
[1]具:备办。鸡黍:《论语·微子》:荷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黍,黄米。具鸡黍:款待之意。
[2]轩:窗。场:打谷场。圃:菜园。
[3]就菊花:赏菊的意思。就,近。
谈孟浩然《过故人庄》【2】
林庚
这是孟浩然的名作。特别是前四句给人印象最深,这四句并曾以一首绝句的形式,误入王维集中,也可见这首诗与王维的作品很相近。王、孟并称,相沿已久,这是由于后人特别强调王维隐逸诗的缘故。其实即使就隐逸诗来说,王维的风格也显然与孟浩然有别,前者比较自然朗爽,后者比较深远清峭。至于王维其他的方面,如一些边塞的主题,七古的长篇,七言的绝句,就是五律中像《观猎》《送赵都督赴代州》等,都与孟浩然相去颇远。孟浩然大部分诗作都集中在隐逸一类的主题与五律的体裁上,一种谨严洗炼的风格,往往给人以更深的孤独感。他的冷峭之中有时甚至于是激切的,像他的名作《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山瞑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数行泪,遥寄海西头。
这里的形象也是王维诗中所少见的。而孟浩然的风格正是在表面的幽静中注入了深深的不平,这是和他一生的遭遇与性格分不开的。当然孟浩然也偶然会有一些天真忘怀之作,这首《过故人庄》就是其中的代表。
要说明这首诗的天真忘怀,最好是举孟浩然的另外一首诗《秋登兰山寄张五》来对照一下: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这也是名作。可是这首诗中,诗人是孤独的。他虽然“时见归村人”,却只能“隐者自怡悦”。他在山顶上望见了那么美丽的人间,而自己却只能在白云之中。正像《招隐士》中所说的: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3】
山中尽管高洁,诗人却不能不感到一些清冷。所以这首诗与《过故人庄》虽然最后都归结于希望在重阳节的时候与友人共饮,可是一个是在寂寞的山中,一个是在人间的农庄;一个是以清峭的心情在期待着温暖,一个却忘怀于友情与大自然之中。孟浩然大部分的作品其实正是属于前者。这首《过故人庄》因此表现了一个寂寞的诗人到了人间所能获得的喜悦,而这个人间只有在素朴的农庄中是存在的,也只有这个素朴的农庄才真正能够接待我们不幸的诗人。
陶渊明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归去来辞》,写诗人把官一丢而跑回农村去,那时充满了多么喜悦的心情。我们在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过故人庄》中,孟浩然是那么充满了喜悦的。正是这个喜悦让孟浩然歌唱出一个和平生活的美丽的农村,这美丽,也只有那素朴的心才会真正地深深感受到。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庄,既没有引人注目的名胜,也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眼前不过是一片场圃,一片桑麻,一些村人来往的道路。谁真正爱这个天地呢?而孟浩然确是写出了这个淳朴的天地。这里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诗人,写出一个天地是不容易的事。这里要真正全心全意地歌唱它,要诗人的世界观与农村淳朴的生活有高度的统一,于是通过诗人的内心世界再现一个典型的和平的农村、一个理想的天地。这里孟浩然并没作任何更多的表白,它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告诉了我们。
要进一步地理解这首诗,就还要更具体地通过诗句的分析。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似乎很平淡,它的素朴的语言与素朴的田家款待,所谓: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让全诗在一个平民生活的气氛中展开,这对于全诗是一个良好的开始。通过鸡黍这样具体细微的事物的描写,唤起了整个田家的形象。这里是谐和的,真实的,而又是开展的。于是出现了那千载流传的名句: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这是全诗的灵魂,思想情感与艺术形象交融的顶峰。要知道这两句诗真正的好处,我们这里引一首马致远《双调夜行船》中的几句:
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竹篱茅舍。
这也是散曲中的绝唱。如果分开来看,马致远的诗句可能更容易引人入胜,因为这里刻画得更新鲜。可是一对照起来,我们就会觉得孟浩然的诗句更浑厚些,它丝毫没有露出怎样加工的痕迹,然而整个农庄历历在目,这里表现了更深的工夫。这当然也由于马致远是从一个茅舍的角落来写的,这是一个隐者小小的天地,然而这小小的天地却与大自然一脉相通,这正是那可喜之处。而孟浩然所写的却是整个农村,在这里孟浩然的诗有更多的人间味,在更为普遍的天地里有更多的生活气息,这也就是所以更为深厚的缘故。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不但写出了层次分明的近景和远景,而且这围绕着村落的绿树与斜倚在绿树之外的青山,正是相映成趣地表现为一种谐和而单纯的美。这里我们无妨说它们是在心心相印着,所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那绿树像母亲的温柔,怀抱着这个村落;而那青山像一个岗哨,远远地也注视着这个村落。它们的心全在这个村落上,因而那城郭也就被冷落地丢在一边了。这里我们才明白,既然说“绿树村边合”,已经是在城郭之外了,为什么还要说“青山郭外斜”呢?这诗句正在于陪衬出那城郭的不重要来;青山、绿树、村落,那么水乳交融地打成一片,那城郭就只好若有若无地默默靠站在一边,这真是再亲切也没有的一幅图画。而与这同时,通过那青山的顾盼,通过那绿树的环抱,对于这个村落,我们将感到多么亲热啊,仿佛我们早就该认识它们了。于是我们感受到每一块草地的绿色,每一片庄稼的成长,每一条小路上的泥土气息。这些,诗中都并没有写,它却存在于青山的一瞥与绿树的拥抱之中。而我们不幸的诗人,像一个贫困的孩子,忽然到了真正心爱的乐园,他要东看西看,东问西问。于是: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这里他不知有多少话在说呢。他忘怀于这个面前展开的天地之中了。于是: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他说他下次还要再来。他当然是要再来的,这难道不是最诚恳最动人的语言吗?凡是稍有童心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孩子在要离开玩了一整天的心爱的地方的时候,那天真的心将要说出什么。“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片天地将永远生活在诗人的心里,这首诗因而也就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原载《语文学习》1957年第2期)
与诸子登岘山[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2]。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3]。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注释
[1]诸子:指同游的几位朋友。岘(xiàn)山:在湖北省。
[2]“人事”四句:人事,指人的活动、事业,等等。代谢,新陈交替。往来,旧的去新的来。胜迹,著名的古迹。
[3]“水落”二句:写深秋眺望所见。“天寒”句意谓天寒水清,始觉湖泽之深。梦泽,即云梦泽,古泽薮名,在今湖北省境内,其范围各说不一。
回忆者与被回忆者【4】
斯蒂芬·欧文
每一个时代都念念不忘在它以前的、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纵然是后起的时代,也渴望它的后代能记住它,给它以公正的评价,这是文化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如果后起的时代同时又牵涉在对更早时代的回忆中——面向遗物故迹,两者同条共贯,那么,就会出现有趣的叠影。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发现过去的某些人也正在对更远的过去作反思。这里有一条回忆的链索,把此时的过去向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有时链条也向臆想的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记起我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当我们发现和纪念生活在过去的回忆者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回忆我们自己也成了回忆的对象,成了值得为后人记起的对象。
回忆的这种衔接构成了一部贯穿古今的文明史。孔子要我们“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要“作”的是生活在远古的圣人,他们是文明的创始人。“述”则是后来的最出色的人,也就是贤人的任务。在声称他只述而不作时,孔子也在无声地教导我们要以他为榜样,而在这个教导中又潜藏着另一重真理:如果孔夫子只作而不述,后来时代的人就会追随这种榜样,大家都会去“作”,而不屑于回忆和传递已经做过的事(而且佯装不记得他们所要记起和效仿的、有影响的“作”的榜样)。通过把“作”和“述”的概念对立起来,孔子提醒我们,已经做成的事仍然是脆弱的,如果不是经常主动关心它,它还是会被抹掉的。只有得到不断传递下去的许诺,人类的行为才有希望超越有限的现在而继续生存。
有一些场景可以使得回忆的行为以及对前人回忆行为的回忆凝聚下来,让后世的人借此来回忆我们。在这类场景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岘山上的“堕泪碑”了,这块碑是襄阳的老百姓在公元三世纪中叶为父母官羊祜立的。《晋书·羊祜传》告诉我们: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羊祜去世后)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飧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这块地方不仅仅是积聚回忆的场所;它变得同羊祜本人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回忆前人的行动分不开了。从表面上看,人们回忆羊祜是由于他的德政,但是,同这块纪念碑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这块特定的地方和它作为“堕泪碑”的名声,它们把它同发生上述那件逸事的特定场合连到一块儿。羊祜为了无名的先人而感慨,后人则为了羊祜这个名字而流泪,在这个名字里,人们回忆起羊祜的德政和他的那次著名的回忆先人的行动。如果我们想要为了某个具体的,而不是无名的先人挥泪感慨,那么,就必须有这么一块刻有碑文的石碑,一块起中介作用的、给这个名字和山上这处具体地点染上特殊色彩的断片。
羊祜所以没有被人们忘掉,不光是因为他为了让别人记住他而做了某些事;不朽的声名是其他人出于各自的原因而赠与他的。最初纪念他的是襄阳的百姓,因为他担任地方官时与民为善,深得人心。不过,最终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访问者来到这座碑前流泪,则是回忆起了他对无名先人的回忆。他具体体现了回忆前人者将为后人所回忆这样一份“合同”,这样的“合同”给后世的人带来了希望,使他们相信他们有可能同羊祜一样,被他们身后的人记住。如果得不到这份“合同”的担保,你就同无名的先人们一样,不但人死了,名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你曾经存在过。
从表面看,羊祜留在后人的记忆里,靠的是“三不朽”中的“立德”;是别人把碑文刻在石碑上。而后人通过回忆羊祜,只需“立言”,就能把自己的名字刻到回忆的链条上。在回忆羊祜方面,孟浩然可以称得上是位了不起的回忆者,他的《与诸子登岘山》写道: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代谢”就是某一事物取代另一正在枯谢的事物。这种循环代谢的过程正是谷物生长的过程、季节更替的过程、羊祜所感慨的先人更迭登场又相继湮灭的过程,甚至也包括国都化为黍地的沧海桑田的朝代更替过程。在与人有关的事物中,留存下来的只有“名”,或许还有“铭”——至少目前仍然存在(“尚在”)。
孟浩然的诗使我们恍如置身于一场追溯既往的典礼中:所有在我们之前读到“堕泪碑”的人都哭过了,现在,轮到我们来读,轮到我们来哭了。行礼如仪,每一种典礼仪式,都是一种固定的行事方式,按照《周礼》所说的,这种固定的行事方式,是源自人类共有情感的合乎自然的规范方式。一定的典礼仪式总是与一定的特殊场合有关——婚嫁、伤丧、迎新除旧——而且,在举行典礼的过程中,参预其事的人只是适应这种场合的一个角色,按照这种场合的要求而承担某种功能,他在其中不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在举行典礼的过程中,所有东西的个性都被淹没了,在那种适应这样特殊场合的、人类集体的、合乎规范的反应里,任何有个性的东西都变得暗淡无色。正因为有个性的东西消失不见了,同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反复进行;正因为有可能反复进行,典礼仪式才有可能存在。
孟浩然这首诗的题名叫做《与诸子登岘山》。他在这里所代表的确实不仅是他自己,他说的是“我们”的事,而不是“我”的事。不过,这首诗在很大程度上系念于人的声名,系念于同个人有关的东西,系念于它们是否尚存。在仪式的诸环节中,羊祜的名字是关键的一环:昔日羊祜结伴来到这个地方,为被人遗忘的先人而感慨,今天,我们像他身后所有其他来过这个地方的人一样,如同羊祜当年那样,结伴来到这里,为他而掩泣。“人事有代谢”;我们为一个人的名字所引导而开始我们追溯既往的典礼,这个名字为一则铭文所记载,它不会被人遗忘。这个名字是联结无名无姓的过去和有名有姓的未来的纽带:我们记住了记忆者。
山上和山下四周的风景都使人联想到一些名字,给人带来若干具体的回忆:“鱼梁”使人想起汉末居住在岘山之南的隐士庞德公,“梦泽”让我们想到诗人屈原——放眼望去,触目都是胜迹。由于这些往事在我们记忆中留下的痕迹,我们欣赏风物景致时就有了成见,处处要以眼中已有的框子来取景;我们站在岘山,举目四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可能再是抱朴守真的自然景色,历史已经在它身上打下了烙印。在人们的相互往来中,有人已经使得他们自己的某些东西同永恒的自然联结在一起,留下了孟浩然诗中所说的这种“胜迹”。
诗人的目光掠过鱼梁梦泽,在回忆中激起阵阵火花,不过,只有当他的目光从四处环视中收回来、转向石碑时,我们才遇到这首诗所提到的唯一的一个人名:羊祜。羊祜也同我们一样放眼四望,也看了鱼梁梦泽;在前六句诗里,我们做他做过的事,感受他感受过的情感。此时与彼时的区别在于这座石碑,在于刻在上面的名字和隐藏在它背后的、《晋书》告诉我们的那段逸事。区别在于:羊祜登高、眺望,然后流泪;我们阅读、登高、眺望、读碑文,然后流泪。这里,是“名”和“铭”把我们的经验联成一体。直到“读罢”,我们才流下眼泪。我们站在山上,大声读着在我们之前许多人读过的关于羊祜的事迹,脚下正是以前许多人站过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朗读的过程中,伴随着这种自发的、重复了多次的、大家共同的仪式性的举动,出现了有个性特征的名字,以及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个有自己身份和特征的人。
在朗读碑文时,人们回忆起了回忆者。孟浩然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回忆起回忆者的,而他自己又把自己回忆的行为铭刻在他的诗里,对我们读诗者来说,他又成了回忆者。这首诗是孟浩然最著名的诗之一,是使后人回忆起他的诗之一。在他以后的唐代诗人,当他们游览岘山时,所回忆起的就不会只是羊祜了,他们会常常忍不住想同孟浩然唱和,或是因袭他的作法。
孟浩然想要在这片风景中占有一席之地,让他的身影重叠在羊祜的身影之上。但是,对后来的人来讲,这片风景所承担的名字太多了;在它之中挤满了多得举不胜举的来访者,其中不乏高风亮节的士子、情溢言表的墨客,有人如愿以偿,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有人写上又被涂掉,一无所得。已经没有后来人的插足之地,可以让他们写上自己的名字。大自然变成了百衲衣,联缀在一起的每一块碎片,都是古人为了让后人回忆自己而划去的地盘。
人们热衷于把最初的杰出的回忆者们的名字铭刻下来,既刻在石碑或者其他纪念物上,也刻在自然风景上,当然,后者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自然场景同典籍书本一样,对于回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时间是不会倒流的,只有依靠它们,才有可能重温故事、重游旧地、重睹故人。场景和典籍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它们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间,人的历史充仞其间,人性在其中错综交织,构成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人的阅历由此而得到集中体现。它们是看得见的表面,是青葱的黍田,在它们下面,我们找得到盘错纠缠的根节。然而,在地面上它们是主人,它们排挤那些后生的、不如它们强壮的、想要插足于此地的生长物。
注释
【1】周振甫(1911—2000),学者、古典文学专家、资深编辑家。著有《诗词例话》《文心雕龙注释》《中国修辞学史》等。经他审阅编辑的书稿有《管锥编》《管锥编增订》《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楚辞补注》《酉阳杂俎》等。本文选自周振甫《诗文浅释》,见《周振甫文集》第九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2】选自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文选》卷三十三。
【4】节选自斯蒂芬·欧文《追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