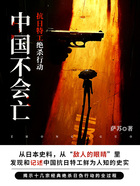
代序:大爱之杀——从一个错误说起

他们有的是国民党人,有的是共产党人,有的,什么党派也不属于。他们共同的地方,不过是中国人而已。
写作抗战特工题材,是我一直的一个心愿。
在八年的卫国战争中,除了在前线与敌浴血苦战,中国的特工人员,也曾在敌后展开积极的活动。爆破,暗杀,情报,宣传,这些大多数年轻而坚定的中国人,在敌人的后方,如同钉子一样存在,向敌后的百姓们证明着中国不会亡的真理。
他们的牺牲是巨大的。
在日本,如果你今天去买家具,想到家中有某个空隙似乎可以容纳,却又没有把握,那么,你只管去买。因为日本所有的房产商和家具商都是按照十分的规矩来制造他们的产品,因此,不同家具拼起来的尺寸必与房间墙壁的长度吻合。
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深知这是一个细致到令人难以承受的民族。当这种细致,与法西斯的残忍凶狠结合起来,可以想象将给中国的抗日军民带来怎样的伤害,也注定了我国特工人员在敌后的行动何等艰难而危险。
然而,我们的好儿女还是去打了。
唐绍仪,傅筱庵,俞叶封,陈明楚,何天风,一个个大名鼎鼎的汉奸命赴黄泉。
天马号,出云号,一个个威风凛凛的巨物在爆炸声中颤抖。
交通员在敌人的战线上穿行。
伪造的日钞在敌后的市镇上投放。
中国特工人员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敌后打开一个新的战场,这段历史中渗透了太多的传奇,精彩和牺牲精神。
那么,从哪里开始呢?就从老萨所犯的一个错误说起吧。
2004年,我写作过一篇《碧血神枪》,描述了抗日杀奸团在古都北平的行动。这大约也是多年来第一篇对这个团体进行描述的记述性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似乎这才意识到,当年曾有一批如此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沦陷的北平和天津,向日寇和汉奸打出了无畏的枪声。
然而,这篇文章中却有一个错误–我将抗日杀奸团的重要成员袁汉俊写成了“袁世凯的侄孙”,袁汉俊烈士的妹妹写来信件,与我澄清此事,说明袁汉俊与袁世凯并无关系,信件如下–
关于胞兄袁汉俊的简况
我家世代书香门弟,祖父袁蓉生。民国初期携带家眷从家乡浙江上虞到上海谋生,当了沪汉某轮船的船长。父亲袁英辛191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工系毕业,后为瑞士雀巢奶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届时父亲仅20岁。“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父亲调到天津分公司。程案后,为保护祝宗梁和我父亲的安全,抗团的曾澈护送祝父和我父去重庆见戴笠,戴有意让我父亲在重庆工作,但父亲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执意返沪。
袁汉俊是我的二哥,他年长我14岁,关于二哥抗日的事情,是我长大后从长辈的谈话中才知道有关二哥的点点滴滴。二哥天资聪明、秉性善良忠厚、耿直侠义,富有爱国热忱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记得1934年秋,那时我三岁,家住天津万国桥(现今解放桥)附近的一座西式小楼里,一墙之隔是法国工部局。二哥常带我至家屋顶的大平台上玩,他总是面朝工部局,面色凝重地倾听工部局发出的拷打声和凄历的惨叫声。那时我很奇怪,不懂二哥为什么要听这吓人的声音,事隔多年,我才知道那声音是爱国志士和抗日青年被严刑拷打的凄惨的喊叫声。这说明二哥在南开中学时期就激发了抗日的爱国热情,从此他走向抗日救国之路,最后英勇牺牲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
我二哥与抗团成员的祝宗梁、孙大成、刘友琛、冯健美等多次进行抗日杀奸活动。如火烧日军的粮库和棉花栈,爆炸日军收买的光陆电影院、中原公司和日军设的公共汽车。刺杀程锡庚和王竹林等几位大汉奸。在刺杀程锡庚活动中二哥是主要人物之一,因而引起敌人的注意,多次追杀他。
程案后二哥去重庆大学读书,1941年他给抗团的女友信中称:“我虽身在读书,但心仍在抗日……”在他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二哥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北平,以实际行动继续抗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1943年初,被叛徒郑有溥、齐文宏出卖,在二哥由上海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天津火车站被日军抓捕。因为二哥是抗团的骨干,知道抗团全部情况及成员名单,他知道如果屈服招供,抗团组织将被破坏,所以在敌人的酷刑下,二哥宁死不屈、丝毫未吐露半点组织机密。慷慨就义时,时年26岁。据牢狱的室友说:“袁汉俊临刑前,见到狱友冻的发抖他把身上的皮衣脱给狱友,而自己只穿单衣走向刑场。”由于敌人的残忍,致使父亲和亲友四处寻找终未找到尸体。
据抗团的同志称:“袁汉俊为人忠诚,工作积极负责,那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那里,对抗团贡献很大,沈栋被捕后,有关组织,总务财务等工作他全部承担,将团员名册、钱务等存放在法租界新华银行的保险柜里,他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工作稳健任劳任怨。”
写文章写出了错误,萨连忙道歉。
此错何来呢。说起来是我错信孤证造成的–为了解冯运修牺牲的情况,我通过北京政协和在台湾的朋友,联系了曾经涉及抗日杀奸团组织工作的旧军统人士。对方提供了如是情况,应该说老先生提供的大部分情况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也不免出现上面的错误。现在既然出了错误,自然要找对方核查。因为提供情况的老先生已经过世,同其后代谈起此事,分析当年也曾出生入死的老先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可算是与其职业有关了——第一,老先生是军统出身,但实际抗日杀奸团只是个别人员与军统有关系,对其全貌他并不了解;第二,他当时并不是在平津活动,而是在保定,所以所述不免有风闻的内容;第三,当时军统确有说法,讲平津有袁世凯的后代在参加抗日活动,于是老先生凭逻辑推断这就是袁汉勋和袁汉俊。错误是不应该,萨因此向烈士的家人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但是,继续追踪这个错误背后的东西,却让我颇为吃惊,甚至重新认识了当时平津的抗日形势–原来,这位老先生虽然搞错了人,但有一个事实他并没有弄错,那就是袁世凯家的确有人在平津参加抗日活动!
参加抗日活动的不是袁世凯的侄孙,而是他正牌的孙子–此人,就是当时北平地下党中的风云人物,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
此外,袁世凯还有一个孙外甥也积极参加抗日,正是抗团骨干孟庆时所在的育英中学同学,此人就是后来的中央党校教授艾克力!
正如这个例子表现出来的,中国的抵抗者覆盖了中国的各个阶层,而且,每一个阶层都不乏慷慨赴义的英雄。
这是此事引出的第一个没想到,第二个没想到是袁汉俊烈士的亲人并没有责怪我的疏忽,反而诚恳地介绍了去与抗团中著名的“书生杀手”–祝宗梁老先生联系。
祝老先生,又不顾高龄,认真地为我写下了一篇六千字长文,谈了他和袁汉俊烈士在那些铁与火的日子里,怎样并肩作战。
此文如下–
我和袁汉俊在一起
祝宗梁
我们的第一个定时燃烧弹是刘福庚和李宝仁制造的。不幸出了意外,他们一死一伤。制作方法还是保留了下来。以后孙若愚和袁汉俊就按着这方法又制造了两个,这就是后来破坏日商光陆、国泰两家电影院用的。以后又计划破坏日商中原公司,再要制造六个燃烧弹。他们就约我也来参加工作。这就使我和袁汉俊经常在一起工作,一直到一年以后,我们又一起离开天津去到内地。
在执行破坏中原公司的时候,孙若愚编了六个小组,每个小组两个人。汉俊又是和我在一组。被指定的地点是西装部。孙若愚说:“这里最难,所以就分配给你们。”这里的确难搞。一间大屋子,所有商品都在柜台后面的橱窗里。没有顾客,几个营业员都闲着没事。我们在未进去之前,就先商量一下对策。汉俊说:“我们分头进去。我设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找机会放(燃烧弹)好了。”后来我是把它放在一匹被打开展示的衣料后面的。
抗团在逆境中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战争爆发才半年多,就有些人离开了抗团。有人是因为搬家或异地求学,但还有人是主动离开的。当然抗团本身工作不到位,也是一个原因。无论如何这个工作是艰苦的。还要冒不少风险。而且又无利可图。如果空有雄心壮志,对个人利益又是那么关注时,就会产生动摇。袁汉俊参加抗团很早,对那些不辞而别的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我时而流露出一些批评之词。汉俊本人就一直团结在同志们身旁,奠定了抗团的发展。
袁汉俊从开始就担负抗团的总务工作。他把人员名册,用他自己的密码,全部翻译成数字,并保存在银行保险箱里。
抗团开始时是没有经费来源的。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如纸张、油印机、……都靠大家捐助。在这方面汉俊是从不要别人开口,他就把一切安排好了。后来抗团得到一些奖金,也都由他保管。
沈栋被英工部局逮捕,在搜查时被发现了証据(据说是手枪)。沈栋不得不承认他是进行抗日活动。这也就造成他不能被判刑,又不能被释放的情况。沈栋在狱中对看守他的巡捕仍在宣传抗日。使马从云自愿参加抗团。此后沈栋和组织一直保持联络。都是由马从云替他与袁汉俊之间传递信件。
后来李如鹏代替了沈栋的工作。这时成立了抗团干事会。曾澈负总责、李如鹏负责组织干事、孙若愚负行动干事、袁汉俊负总务干事、我负技术干事。沈栋的名额仍保留在干事会里。
要我担任这技术干事,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因我曾参加制造过定时燃烧弹,也就是我具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但这远不够的,于是我就考虑买些书来学习。袁汉俊又主动为我找来不少书,有的是从刘福庚那里拿来的,又买了一些。应该说担任这工作的应是汉俊和我两个人。
我们考虑到将来要烧什么,就用什么样的燃烧弹。例如棉花,用小型的就可以了。我们设计制造了一种如香烟盒大小的燃烧弹,用力丢可以有二、三十米远。这就可以从外面丢进去,我们不必进入现场。在学校化学课程里学过,黄磷在常温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燃的。于是我们用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当引燃剂,这二硫化碳蒸发需要几秒钟时间,这就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平安地离开现场。
我们在书里看到苦味酸有爆炸的性能。就考虑用苦味酸来代替雄磺与氯酸钾的这种炸药。因为这种炸药很不安全,稍有磨擦或碰撞就会爆炸。我们利用氯酸钾有释放氧的功能,在一定的比例下与苦味酸混合。在用力的打击下,就可以爆炸,而且威力不小。
我们还做了个更小的燃烧弹。把麵粉和氯酸钾混合,加水调和做成小球。等它干燥后,再蘸一下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用弹皮弓弹出去,可以有四、五十米。没想到它爆炸了。我们还在试验室里造出了雷汞。和氯化苦剂的催泪剂。但这些都没有机会利用上。
孙若愚和我分别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多想些,到正式工作时就不分家了。有事大家干。人手不够就找人来帮忙,没有说不愿干的。在组织内没有上下级。工作时也没命令。谁愿意谁就上。大家都是自愿来的,完全义务性质,都没有工资。
有两次放火,我都没找袁汉俊。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那时我觉得他就缺少运动员那股灵活劲,很斯文不像当个行动员。孙若愚的行动组的组员,个个都身强力壮、打斗好手。一天,我们预备晚上放火烧棉花栈,这次由第二小队执行任务。我想若能把他们的消防破坏掉,就会有更大的战果。这时正好袁汉俊来了,于是我就约他一起去执行这任务。我准备了一瓶王水,想把它浇在消防水龙的帆布带上。那天傍晚,我们到了消防站。大概是吃饭的时间,只有一个人在看守。汉俊假装问路,弄不懂还请他指点。我就趁他们站在门外的时候,把王水都浇到水龙的帆布带上。这是直径有一米多可转动的大轮子,并排绕着十几盘水龙带。至少有六、七条被浇上王水。王水一碰到帆布,颜色立刻变黑了。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转动轮子把黑色部分转到后面去。那天棉花烧起来后,我隔了几条街看到把天都照红了。可是没去看他们救火,这次破坏的效果也不了解。
程锡庚是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径理,还兼海关监督。制裁程逆这件事,起初都是孙若愚调查的。在1939年4月初,孙若愚要去北平。他临走前向我说,要我留心这件事。他调查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大致是:程本人五十几岁、秃顶、戴金丝边眼镜。有个女儿在耀华初中读书。他家汽车号码是1657。爱好看电影,准备在电影院制裁他。4月9号星期天,袁汉俊、孙惠书、冯键美来我家玩。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要回去。我拖着他们一起到各电影院转转,看看有没有1657的汽车。居然在大光明电影院发现了它。
我们立即决定行动。我回去取枪,汉俊去找刘友深来帮忙。等都回来,电影已经开映很久了。中间休息时,我们分头到楼上、楼下去找。只是在楼上中间第五、六排发现一个可疑的对象。跟着电影又开映了。可疑的是他们有五个人。夫妻俩带三个孩子。大女孩十二三岁,正是读初中的年龄。另外还有两个男孩,都还是十岁左右。我们事先并不知他家还有男孩。我们又谁都没见过他本人,这使我们不敢断定他是否就是程锡庚。
我想把他引出来再行动。我去打个幻燈片。上写“程经理外找”。等我回来,刘友深对我说:这人看了幻燈片,就要站起来。但马上被他妻子按下去了。从这个动作我们断定他就是程逆无疑。我从另一个方向走到程逆后面这排,再往里走距离他两个位子,我坐下来看电影。这主要是使我定定神,把刚才一些杂物事摆脱开。等我决定行动时,立刻站起来。用枪对准他的脑袋只有一尺远。连开四枪。这时四周观众都站了起来。我旁边的几个人都向后退,给我让路,让我先走。
我和刘友深从三楼混在观众中下到二楼的楼梯口时,一个人突然从身后抱住我。我转身用枪对他肚子开了两枪。他倒了下去。又一个人从身后抱住我。我再开枪时,子弹没有了。我们在挣扎中一起滚下了楼梯。两人都是头下脚上,他抱住我的腰,我拢住他的头。他张嘴把我手指咬了一口。汉俊这时过来,用枪顶着他的背后,开了一枪。他身体顿时软了下来。汉俊扶我站起来。我们一起下楼出了影院。
大家都先后回来了。事情虽然有些波折,但还算顺利。李如鹏知道我们胜利归来。就带来好多好吃的来慰劳我们。因为我们都还没吃饭呢!曾澈跟着也来了。听了我们的叙述,他马上就走。他说:他去打听后果。我的手破了,孙惠书拿些红药水和消毒的药膏帮我包紮一下,也没去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看见程逆的家门口挂了白纸条。这就是报丧的表示。报上说:第一个抱我的是个白俄,肠子被打穿了八个洞,送到医院。第二个是瑞士人,当场死亡。他已经买好船票,预备回国。只因多管闲事,意外身亡。这天我仍旧去上学。语文老师王则民把他在报上看见的这消息,再加上他绘声绘色地向全班同学讲述,使全班同学都欢欣鼓舞。我也和大家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之中。当我想到这是我把它带来的,这就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袁汉俊这一枪,救了我的一条命,同时也纠正了我对问题的一些看法。过去我总以为伶俐、反应快、能说会道的人肯定是能干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更应该看到一个人在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再深入一些,还应看到一个人在处理公与私的这方面在他心里的矛盾。如果一个人的私心杂念总在作怪,这种人是绝不能委以重任的。还有一条,就是“沉着”。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不能乱了自己。袁汉俊就具备这方面的优点,他平时多沉默寡言,其实他总是在思考、观查。他比别人深沉得多。他也比别人能干得多。
六月份,曾澈通知我们参加刺程案的几人去重庆。他说这是重庆来的命令。因为这正是学期末尾,我们拖到放暑假才成行。七月,我们买到一条去香港英国货輪的船票,我们几个再加上沈栋和冯键美的母亲一起去了香港。孙惠书因她母亲关系不能走。到香港第二天又乘飞机到了重庆。在重庆戴笠接见了我们。他一直谈抗日的事情,也还带着些大道理。其实,我们这抗日情绪,与什么大道理无关,好像我们从娘胎出生来时就带来了。八月初,戴笠还带领着我们五个人去见了蒋介石。他没说什么话,只讲了“好,好”几个字。
8月15日,戴笠要我和袁汉俊到香港去自首。事因是这样:在天津有四个军统分子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方面就要英租界当局把这四人引渡给日本,理由是因他们是刺程犯。英方说他们不是,所以不引渡。日方硬说是,英方仍说不是。于是就需要我和袁去自首,说我们才是刺程犯呢!我们自首时特别提出证据:(一)我们在那天和瑞士人搏斗时丢失了一支手枪,落在楼梯附近,是六轮手枪,里面有六颗子弹而且都是用过的空壳。手枪上有指纹,这指纹是祝宗梁的。(二),影院里找人的幻灯片上写“程经理外找”是祝宗梁写的,可从笔迹查证。(三),与瑞士人搏斗时,祝宗梁还丢了一只鞋,是右脚的,丢落在楼梯附近,可从气味查证。我们去自首前,戴笠向我们保证说:如果香港受理,我们可能被扣押,在香港也许在伦敦。无论什么地方,将来必定设法把我们救出来。为了避免日本对我们家属报复,所以将我们的父亲接到内地去。
英方香港当局没有受理我们的自首。在香港住了约三个多月后,我们就回重庆了。以后,袁汉俊去重庆大学读书,我去成都进了金陵大学学习。英日双方从此事后,争论了一年多。后因欧战爆发,英国向日本屈服。四个人被引渡了,英国还封锁了滇缅公路。
1941年10月份,孙若愚在上海出事。他被炸药炸断了左臂,钱致伦眼部受伤,伤后还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袁汉俊知道这事后,就通知我到重庆去商量如何处理。我去后,我们决定一起去上海。沈栋在成都又介绍申質文、向传纬二人和我们同去上海工作。这时还有方佩萱、石月珍二人是从上海来的,她们也要求一起回上海。我们六人到11月底才成行。我们坐飞机到了香港,想乘轮船去上海,可是一直没船。又等了几天,突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日军从陆地和海上南北两方面进攻香港。我们听说英国人要马来西亚人打第一线,要印度人打第二线,英国自己打第三线。马来西亚人不肯送死,日本人一来,他们就退。第一线败退,第二线跟着退,英国没打就退到香港一个孤岛,九龙地界全被日军佔领。这一仗,也只有十几天。接着日军又要攻香港。在九龙尖沙咀附近,有个大油库。那时候有许多大油罐建在那里。英军就向这些油罐开炮。日军向香港也开炮。终于油罐起火了。那时候,我们就住在尖沙咀的一个旅馆里。油罐大火的黑烟,把白天挡成黑天,晚上,火光又把黑夜照成白昼。除了这些,还有炮火、还有的地方被烧着的火。还有炮声、机枪声隆隆不断。这就是战场,但我们没看见士兵。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又没几天,也就是1942年以前,战斗就结束了。香港的战争只用了二十天左右。
香港未沦陷前,军统的香港单位通知我们说:有飞机回重庆。要我们随时准备好,等待通知。只能人走,不可带行李。可是一直没等到。最后给我们一笔旅费要我们自己设法离开香港。(这件事后来听说,飞机不是没有,只是被孔二小姐把她的狗和家具用飞机运到重庆。留在香港的国民党好多大人物都没有离开香港。为此,各校大学生罢课,游行,要打倒孔祥熙。)我们觉得住在旅馆很不安全,就设法搬出去。后来找到一处空房,是英国人一家的住处。英国人逃走,把房子交给保姆看守。这保姆就租给我们用。就先把两位女同志安排在这里。男同志以后也陆续搬出来。日本佔领香港后,放假三天。这三天发生了什么事?没人报导,以后也没记录。我们后来听说,一天来了两个日本兵,到旅馆要找姑娘。万幸我们早走了一步。
我们怎么办?是等还是走,大家都没有主见。香港这时物价飞涨,粮、油、菜都贵的要命,而工业品又便宜得没人买。后来得到一条出路:香港的盗匪帮有人可以带我们离开这里,就是走。要走好多天,到内地的广东惠州。条件是我们要拿出一笔保护费。这一路他们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行李,每人一件不可太大,可由他们运。这件事我们一起商量,各有不同想法,特别是要用腿走,女同志可以吗?最后决定:走。
1942年2月初,我们六人再加上在香港遇到的抗团同志,有吕乃灏、孙克敏、宋显德和宋的亲戚宋允泰,共计十人。走了八天到了惠州。这八天里,遇到一次抢劫,抢劫的是日本兵。那是路过封锁线的时候。这八天,我们是有什么就吃什么,晚上,有屋子就睡屋里,没屋子就露宿街头。半路上看到不少逃难的,也看到遇难的死人。总之,我们是平安地离开了香港。
在惠州正赶到春节,以后又乘了八天船。到了河源。又转乘汽车去韶关。在韶关才有政府的组织。我们得到通知,说:方佩萱和石月珍的身份泄露,不能再去上海,于是我们把她俩送到柳州。她们与宋显德等人去了重庆。我们转道去浙江金华。我们在乘汽车的路上,碰到广东百年不遇的大雪。有个广东人说他这辈子还第一次看到下雪。
在金华遇到从上海来的钱致伦。他和孙若愚被法工部局逮捕后,又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在敌人残酷的刑讯下,吃了不少苦。因为没有口供,被营救出狱。这时又值敌人发动浙东战争,金华不久沦陷。我们坐在拆除铁轨的最后一班火车离开金华,到了江山才与军统的单位相遇。这时抗团有个暑期训练班成立,要我回去参加。到这时我不得不和袁汉俊别离。同时,袁汉俊带着几位同志在军统的帮助下去到上海。我和钱致伦去暑训班。
1942年冬天,军统要我去上海为他们办一件事。1943年1月中旬,我到了上海。我见到申质文,他告我电台被破坏了,还说袁汉俊去了天津。我按着规定的办法给汉俊写封信,希望他回来。过了几天,天津的郑有溥来上海。这人我听说过,但未曾会过面。他和申质文、向传纬见面时,我也参加。我们正在一家饭馆吃饭时,突然许多便衣将我们包围。我们就被押送到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我在被审讯时,我不承认我是祝宗梁。日本宪兵说有人都供出来了,他还把他的记录给我看。我在上面看到有“蔡世光”几个字,我知道了是郑有溥出卖了我们。不但我们上海出事,连天津抗团也出事了,袁汉俊也一定被捕。蔡世光是我和汉俊约定的我的名字,给天津的信就是用这名字写的。在以后的审讯中,我一口咬定我不是姓祝。因我有张身份证,名字叫张志宏,其实这是花钱买的。日本宪兵是相信他们的审讯方法,在拷打中是没有不招供的。经过三天的拷打,还用了灌凉水、火烧、泡在冷水里等,我始终说我是张志宏,他们把我弄错了。就这样他们就对我定了案。上海抗团这次有九个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申质文受刑最重。罗长光、向传纬也相当厉害。从前军统的毛森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被敌人逮捕。他就投降成为日本宪兵队的特务队队长。专门帮助敌人逮捕共产党。与此同时,他暗中仍和重庆有秘密联系。三个多月后,申质文、向传纬、陈泽永三人被毛森保释,其他几个就教育释放了。
陈肇基在1942年从北平的敌人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天津又准备把从前的抗团恢复。他做了些联系工作,但感到没有力量的支援,无法坚持很久。于是他去到界首,和抗团在界首的联络站的沈栋取得联系。沈栋当然热情支持,同时还说袁汉俊在上海,并将联络地址都交给了陈肇基。过去陈肇基就与袁汉俊相识,现在又是旧友重逢,他当然很高兴。他没回天津就去上海找到袁汉俊。经过他一说,袁汉俊就同陈肇基去了天津。就在他们恢复抗团组织的同时,遭到齐文宏、郑有溥的叛卖,以致全部被破坏。这两个叛徒,齐文宏是主谋,但他与抗团关系不深。郑有溥是他妹夫,曾在组织里担任一部分的责任。这次天津抗团大约有二十多人被捕。袁汉俊在香港自首时就有底案,敌人肯定饶不了他。自抗团开始,汉俊就是个骨干,他知道抗团所有的事。真不敢想象,他在敌人多么残酷的刑法面前,吃了多少苦。我们相信,他是坚决保护了抗团的机密,上海抗团只有九人被捕,这只是由郑有溥牵连到几个人,还有许多都没有出事。他不跟我一样把一切都赖掉,有那么多人都认识他,这都是人证。最后听说他在临刑前,他看到一位狱友冻得在那里发抖。他把身上的皮衣给了他,他自己只穿了单衣走向刑场。
2009年9月
应该说,正是这段文字,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些在敌后的抵抗者,是用怎样的英勇和机智,用他们的热血和赤诚,保卫着这个民族的生存。
在我所得的资料中,这些曾经奋起抗争的人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组织,有着完全不同的信仰,但是,他们有着完全相同的一点,那就是他们热切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
那么,用怎样的形象,才能描述我心中的那些勇士们呢?
用007是不贴切的,中国抗战的牺牲和残酷不是英国的浪漫可以容纳。
我想,就是袁汉俊烈士牺牲前被他的战友和亲人反复记忆的那一幕吧。那是极其朴素的文字–
他在临刑前
他看到一位狱友冻得在那里发抖
他把身上的皮衣给了他
他自己只穿了单衣走向刑场。
一时间,有一种无法控制自己泪腺的冲动。
我们不是一个残虐的民族,我们不喜欢暴力和强横。
我们抵抗,我们反击,我们流侵略者的血,只因为我们心中有对一个民族,有对人类的不可磨灭的深爱。
在南京日本领事馆的酒宴上下毒,要为三十万死难同胞报仇的詹长林老人,在九十三岁高龄的时候面对记者,用拐仗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
国破家亡之际,中国特工在行动,这就是大爱之杀。
萨苏2010-4-15于北海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