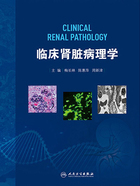
第一篇 概论
第1章 肾脏病理发展史
肾脏病理学作为肾脏病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它的萌芽孕育,发生、发展及成熟,都与临床肾脏病学的发展密不可分。肾脏病学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其间杰出人物如群星璀璨,数不胜数。本章概述一些里程碑式的发现和进展(图1-0-1),无意也无法涵盖所有重大事件及人物。

图1-0-1 肾脏病理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
注:CIBA会议,CIBA基金会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有关肾活检的研讨会。
一、人类早期对肾脏及肾病的探索
人类对于和肾脏病相关表象的初始认知在人类文明发源的摇篮时期便有迹可循。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文化遗址及稍后的古巴比伦,阿卡德帝国等的楔形文字中就发现了有关尿道梗阻、结石、囊性变、狭窄和分泌物等的记述。在著名的古埃及医药大词典(Ebers Papyrus,1550 BC)中有多处提及尿频、尿痛、血尿、尿潴留,以及某些症状与血吸虫感染可能相关。木乃伊的制作也让人们发现了不同的肾脏病变如脓肿、结石、寄生虫及先天异常等。然而,那个时期人们对肾脏以及其他器官的认知多与宗教有关,而对器官的生理功能基本毫无所知。比如在古埃及文化中肾与心被认为是神用于判断人死后是否能重新进入来世的器官。
古希腊语中“肾”(nephro)的词意源于“云”,因“云”可生水,说明那个时期人们已经粗略认识到肾与尿液生成相关。那个时期有关肾病的零星记载多是对尿液的描述。比如流传下来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7)的手稿中有这样的记载:“尿液表面的泡沫常表明了肾脏的慢性疾病”“突发血尿与肾的小血管破裂有关”“无色尿液不健康”,等等。继希波克拉底之后另一位成就卓著的来自古希腊的医学家盖伦(公元129—216)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医学代表人物。他主张解剖是医学知识的基础,并做了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被后人冠以“实验医学之父”的称号。他在动物体中用结扎输尿管的办法证明了尿液由肾脏产生并流向膀胱,并试图阻断血管观察肾脏的变化。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对人体解剖的禁忌,使得盖伦由各种动物解剖发现而引申出的对人体器官结构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误区。
与西方遥遥相隔的古老的东方帝国也用完全不同的思维体系很早就开始了对肾脏功能与肾病的探索。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公元前475—公元前221)中就出现了对肾脏及功能的论述。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记载“腰者,肾之府”,已指出肾脏位于腰部;又如《素问·逆调论》记载“肾者水脏,主津液”,很早便提出了肾调节水代谢的功能。在《素问·水热穴论》中记载着黄帝(公元前2717—公元前2599)与大臣的对话“肾何以主水?岐伯对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并认为肾也主生长发育及纳气。这些理论经历了千百年的实践检验及不断完善,至今仍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医学知识的传播常常伴随着文化的侵略与地域的扩张。在罗马帝国之后的拜占庭王国,伊斯兰王国,以及犹太族裔中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后世留名的医学家对于肾病及尿液的各种观察、诊断与治疗。但此后一千多年直到欧洲文艺复兴,盖伦的医学理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各种临床记录不断丰富着肾病的有关资料但并无质的突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13—17世纪)开始有了人体解剖的记录才最终打破了这种长久的医学发展停滞状态。
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至近代肾脏病学及肾脏病理学发展
(一)人体解剖对肾脏病理的重大贡献
意大利医学家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由人体解剖的发现率先推翻了盖伦对人体肾结构的设想,并最先描述了肾乳头及肾血管分布的初始模型。比利时解剖学家Andreas Vesalius(1514年—1564)由人体解剖观察亲自绘制了700多页的解剖图谱,其中有4页描述了肾脏,并推测尿液是由血液进入肾的空腔再排出到膀胱产生的。在意大利诸多杰出的解剖学家中,Falloppius(1523—1562)和Eustachius(1514—1574)更是将肾大体结构研究到肉眼可见的极限。他们描述了肾大盏和肾小盏,甚至推测出肾实质中的小管结构。第一部具有深刻学术意义并在肾脏病理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是意大利解剖病理学家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1682年—1771年)在1761年发表的《关于疾病根源与诱因的解剖学探讨》。这部专著汇集了作者50年中对640具尸体的解剖分析,收集了尽可能有的史料文献,病例报告,并以极其细致精确的描绘详尽记录了各个器官的病理解剖形态和相应的临床症状。其中对于肾病的记录包括单肾、硬化、软化、化脓、积水、结石、肿瘤、囊性变等,并试图以解剖发现来解释临床表现。例如,其中一个病例临床表现出恶心,呕吐,头痛和阵发性意识丧失;在解剖中发现患者肾脏极度缩小坚硬,外表凹凸不平呈灰色;Morgagni认为是由于肾的病变而导致了患者的上述临床表现。这部系统严谨的解剖巨著奠定了Morgagni“病理解剖学之父”的历史地位。
(二)肾小球和肾单位的发现以及肾脏生理学的兴起
在肾脏病及肾脏病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是17世纪显微镜在观察肾组织中的应用。当时屈指可数的几个使用显微镜的学者中,意大利医生和解剖学家Lorenzo Bellini(1643—1704年)发现了肾乳头中的集合管(也称Bellini管)。意大利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Marcello Malpighi在1666年第一个发现了肾小球。Malpighi通过30倍放大的显微镜发现了肾髓质中的集合管和这些管道最终汇集于肾乳头的开口。他用酒与黑墨水混合注入的办法看到了被他称为“腺体”的肾小球。他生动地描述它们“就像许多果子挂在血管上……,被黑色液体充盈后,看起来就像一棵美丽的苹果树……”,这些精巧的结构被命名为“Malpighian小体”。Malpighi还提出了血液和尿液的分离就是在这些“腺体”中完成并滤出的天才设想。
肾小球的结构问题在175年之后才等到了另一个质的飞跃。当时年仅26岁的英国医生William Bowman(1816—1892)在1842年借助200~300倍显微镜及注射颜料的方法讲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肾小球结构的故事。他发现“Malpighian小体”实际是由一团毛细血管组成,入球小动脉分成多个球袢,在汇集成出球小动脉后再度形成毛细血管网缠绕于肾小管周围,最后形成静脉走出肾脏。他的观察具体到肾小球基底膜和足细胞,当然也包括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肾小囊(鲍曼囊,Bowman′s capsule)及与肾小管的连通。20年之后,犹太裔的德国医生,病理解剖学家Friedrich Gustav Jakob Henle发现并定义了肾小管的薄壁段(loop of Henle)。当时人们对尿液如何产生有不同的解释,以William Bowman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尿液是由肾小球分泌水以及肾小管分泌其他成分混合而成的产物;而与Bowman同时期的德国物理及生理学家Carl Ludwig(1816—1895)综合了微解剖和化学方法印证了Malpighi的推测,得出了尿液是通过肾小球高压高流量滤出并经过肾小管大量重吸收而形成的结论。两种理论各执一词相持了几十年,直到1924年才因Joseph Wearn(1876—1941)和Alfred Richard(1873—1934)的精美实验而终于盖棺定论。Wearn和Richard用玻璃加热抽丝方法做成的微吸管从青蛙肾小球滤过液中采集极小量样品进行分析,发现液体由近端至远端逐渐浓缩,而在肾小管近端的葡萄糖和氯离子在肾小管远端却检测不到,很有说服力地支持了肾小球滤过和肾小管重吸收形成尿液的学说。Wearn在文章中记载,在经过大量练习之后,他终于可以比较有把握的把微管插入肾小球而让管尖停在既不触碰毛细血管袢也不触碰肾小球囊壁的位置上了……,一天下午,……微吸管中收集的液体稳定持续地增多。他和Richard在实验室中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扰动了装置。他们第一次见到如此“大量”的液体。
(三)临床肾脏病学
更早于William Bowman的英国医生Richard Bright(1789—1858)是一位在肾脏病发展史上需要重写一笔的人物。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在临床肾脏病方面集古今之大成者。他有着极高的绘画天赋,格外注重对细节的分析。在1份1827年发表的病例报告中,他对25例水肿患者的病史,症状,化验进行了细致地记录分析和类比。这些患者无一例外地有尿蛋白阳性(以勺子取尿样在蜡烛火上加热出现凝固沉淀),在尸解中发现肾脏显著的病理改变。基于大量临床积累他总结了3种临床肾病表现: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综合征和慢性肾炎综合征。在此基础上,他还做了许多显微镜下组织结构变化(并未发表)及生化检测异常的记录,如肾病综合征与低蛋白血症的关联,肾衰竭时尿排含氮物质减少与相应的血含氮物质含量增高等。他第一个在医院中建立肾脏病房及相关的化验室,并组织了肾脏病专科的医疗小组。这个首开先河的尝试在医疗领域的发展中意义深远。他总结出的肾脏病症状包括蛋白尿、水肿、氮质血症、心脏增大等,被通称为“Bright肾病”。
德国Friedrich Theodor von Frerichs(1819—1885)也许是首位将临床表现与显微镜观察相结合的医学家。之后德国Friedrich von Mueller(1858—1941),Volhard和Fahr等也有卓著贡献。20世纪初,病理学家Theodor Fahr(1877—1945)与临床医生Franz Volhard紧密合作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他们的经典肾脏病理学专著《Bright氏肾病:临床,病理学和图谱》。在这部书中他们首次结合显微镜所见,以病理形态为标准将肾病分为三类:退行性病变,炎症性病变以及血管硬化性病变。后者又分为良性和恶性,良性又根据是否存在肾小球损伤而分为代偿与失代偿;而对于恶性血管硬化病变,Volhard强调了严重血压增高的决定性作用,Fahr则推测或有炎症机制参与,后来被Adalbert Bohle证实这确实存在于少部分患者当中。Fahr还提出了肾缺血导致肾性高血压是由肾脏释放的一种因子引起。这个假设的因子后来被证明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三、现代肾脏病学及肾脏病理学的前叶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科学,技术,发明,文学,艺术各方面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科学技术带入医学领域推动了肾脏病理学的发展。1837年,生理学教授Gabriel Valentin成功做出了薄组织切片,并观察到死于大量蛋白尿患者的肾组织有大量脂肪沉积,“类脂质肾病”(lipoid nephrosis,即现在的“微小病变”)的病名随之而生。1854年更多的染料可供选择用于组织染色。1869年,德国病理学家Edwin Klebs引入蜡块包埋技术并首次提出了“肾小球肾炎”的概念。显微镜的不断改进,组织固定液的使用以及更多科学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总结前人发现,揭示肾病深层病理机制的时代就要到来。然而,当时的病理文献皆是根据尸体解剖所见为主,显微镜检查常常有自溶和被动充血等干扰因素;并且尸体解剖看到的肾病大部分都是晚期甚至终末期,早期或疾病发展期的信息量却是少而又少。我们知道,一个特定的病因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的病理形态改变;反之,一种病理改变也可以由不同的病因引起。这些概念对于当时的人们是无法领会到的,因而对于肾小球肾炎的认知存在无数困惑。除了几类病史与病理发现有明确关联的肾脏疾病,比如糖尿病肾病、多动脉炎、淀粉样变、肾结石、先天肾缺陷等,肾病的总体分类仍旧非常混乱。其中一个例子是1931年由美国病理生理学家Thomas Addis和Jean Oliver合作的专著《慢性Bright氏病的肾脏损伤》。这部肾脏病专著对比1919—1929年10年间72例临床不同种类的肾小球肾炎临床资料和病理改变,包括在活动期、潜伏期、终末期、淀粉样变、肾周炎症、脓肿、血吸虫感染、退行性病变以及血管病变中的肾小球变化。然而,在这部内容丰富详实,逻辑观察缜密严谨的专著中却能感受到一种作者因无法找到根据病理形态而有效分类肾小球疾病的无奈与苦涩——肾功能的变化似乎与形态无关。
动物实验在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医学探索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法在人体中研究肾病发展过程的缺陷。尤其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折阶段,人们认识到炎症不仅与感染相关而且也可以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各种关于肾脏感染及肾自体免疫的动物实验模型更是纷纷建立。在诸多贡献突出动物模型中,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有Theodor Tuffier(巴黎,1857—1929)的肾部分切除对肾结构和功能的影响;Theodor Fahr和Metchnifoff(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的过敏模型;以及W.Lindermann(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建立的自体免疫性肾小球肾炎的模型等。在众多的实验肾脏病理学家中,上面提到的Jean Oliver(1889—1976)有些与众不同。他采取了微解剖的方法从不同动物中完整分离独立的肾单位,并通过灌注各种不同染料和物质成分的液体来逐一解析肾小球和肾小管各个节段的病理形态与功能的变化。他对于肾单位的发生发育与成熟过程的阐释也有着突出的贡献,其中也包括了对肾脏不同发育阶段的枯燥艰苦的肾小球计数工作。
四、现代肾脏病学及病理学发展
(一)肾活检、免疫荧光镜及电子显微镜的发明及应用
肾脏病理学第二次划时代的突破是人体肾穿刺活检技术的发明和应用。1944年瑞士病理学家Nils Alwall首次用针吸的方法成功地为13例患者获取肾组织标本并做出诊断。然而,由于其中一例患者出现并发症而死亡,Alwall决定不再继续使用这项技术,这份首例针刺技术病例报告也被推迟到1952年才发表。与此同时丹麦医生Iversen和Brun,以及古巴的病理同行Pardo也同时进行了肾穿刺活检术的尝试,并分别在1951年及1953年发表了各自的病理报告。针穿刺理念被一些同行采纳改进,其中贡献卓著的应属Robert M.Kark。他与Muehrche和Franklin设计了一种Vim Silverman针,用切取组织代替了针吸,患者也由坐位改为俯卧位,极大提高了穿刺成功率。即便如此,这项技术在初始阶段受到广泛质疑甚至抵触,很多人对于试图用极小的组织做出完整全面的诊断表示怀疑。Conrad Pirani领导的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病理小组系统性的工作对这项技术得到全面推广和认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Pirani小组采取了系列针穿刺取样,揭示了许多肾病发展过程中的病理形态进展及消退;对活动性和慢性病灶的半定量分析也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随后一些有影响力的病理学家也纷纷加入肾穿刺诊断的行列,例如Mount Sinai医学院的Jacob Churg,西北大学的Robert Jennings,芝加哥大学的Benjamin Spargo,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Robert Heptinstall,法国的著名女病理学家Renee Habib等。在我国,赵魁丹等于1958年首先尝试了肾穿刺活检并取得成功。肾活检不但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也为肾病发病机制的深度理解及肾病分类提供了重要线索。新的组织学形态特征不断被确认并渐渐取代了之前以急性、亚急性、慢性之类笼统的以发病期做标准的分类方法,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可重复性并开启了以发病机制为分类标准的可能性。
病理组织学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更多的进步。马松三色染色(Masson trichrome,Masson)和六胺银染色(Jones methenamine,Jones)相继被发明并应用于肾组织切片染色,过碘酸希夫(periodic acid-Schiff,PAS)被用来突出基底膜形态和肾小管细胞纤毛完整性,切片制作也可以达到更薄的2~3μm的厚度。与此同时,Coons和Kaplan发明的荧光显微镜在1950年问世并用于检测组织中的免疫沉积物。1955年Mellors首先将荧光显微镜用于肾组织检查。许多肾脏疾病尤其是肾小球肾炎是免疫复合物介导的。这个新技术让人们首次直接观察到了免疫反应物在肾小球中的沉积以及它们如何导致了各种不同种类的肾脏病。许多新的免疫复合物性肾小球肾炎被发现和命名,例如IgA肾病,感染后肾小球肾炎的补体沉积,膜增殖性肾小球肾炎(MPGN)等,抗肾小球基底膜(anti-GBM)肾炎也由它的特征性的明亮线性染色而被清晰识别。这些新的概念和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被逐渐整合到常规的肾脏病理诊断当中。
电子显微镜也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医疗生物领域。1957年发表了第一篇肾小球病变的超微结构变化报告。电镜(electron microscope,EM)的应用,提供了大量的肾小球组织与结构的新信息,如内皮细胞的网状样穿孔,基底膜的多层结构,肾小球系膜基质和系膜细胞,纵横交织的足细胞足突和滤过裂隙。这个新技术的应用帮助肾脏病理学家们发现了良性血尿家族性薄基底膜病,Alport综合征,微小病变中的足突广泛融合,Fabry病中的特异包涵体“斑马体”,以及免疫沉积物中有亚纤维结构的肾小球病如淀粉样变,纤维样肾小球炎和免疫触须样肾小球炎等。曾经自始至终看似庞大而无序的肾脏病理系统画面至此渐渐变得更加丰富而清晰明确起来。
(二)现代肾脏病理知识的普及与推广
肾穿刺技术的日渐成熟以及同时期的电镜与免疫荧光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对肾小球疾病发病机制以及疾病进展的理解与研究。大量新信息的涌现使得定期学术交流越加成为一种必然趋势。20世纪50年代,伦敦肾脏协会每月在CIBA基金会举行会议,讨论肾穿刺与临床结合的新进展,这为后来1961年在CIBA举行的世界肾穿刺会议做好了铺垫。1961年CIBA国际肾脏病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的29位临床医师与病理学家们齐聚一堂总结交流了大约5 000个肾穿刺的病例经验,讨论肾脏穿刺诊断的利弊和前景,为肾穿刺技术纳入诊断常规并在世界各大肾病中心迅速普及拉开序幕。自此肾脏病理也逐渐从肾脏病学科中成熟为一支与临床肾脏病并重的系统学科。
随着大量新知识的涌现,病理界急需一部能够反映现代病理发展,统一病理分类标准的肾脏病理学专著。1966年,从伦敦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Robert Heptinstall用了3年时间写出了第一版《肾脏病理学》(Pathology of the Kidney)。Heptinstall是诊断兼实验病理学家,他在高血压肾病和肾盂肾炎的科学研究中贡献巨大。书中对各种肾脏疾病首次进行了现代的系统归类,澄清了很多一直含混模糊的概念,所言皆有出处,引用了大量科研、病理、临床文献。这部肾脏病理学专著已再版7次,在现代肾脏病理几代人的传承中一直被奉为最权威的病理教科书。而随着肾病分类的不断细致和增多,“Bright氏病”的用法也渐渐减少直至最终封入历史档案。
五、分子生物学和精准医学时代
从20世纪90年代起,分子生物科学的飞速发展将精准治疗和与之相关的医学理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DNA测序,蛋白质测序,人类基因工程,基因芯片技术等,使个体化诊断和治疗(精准医学)成为新时代的大势所趋。深入的分子机制研究期望能对发病机制,分子标记,疾病分类,预后及治疗有更根本的突破。
早期分子水平的研究理论用于肾脏病诊断和治疗已初见成效。关于膜增殖性肾小球肾炎分类的重新修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组疾病传统上依据电镜免疫沉积物在肾小球中的所在部位和形态分为Ⅰ型,Ⅱ型和Ⅲ型;现在我们知道,Ⅰ型和Ⅲ型中的一部分是由免疫复合物介导所致;而另一部分则是由旁路补体激活途径的失调而导致的C3沉积引起,称为C3肾小球肾炎,与Ⅱ型(致密物沉积病)一起合称为C3肾小球病。补体激活旁路中不同的遗传基因变异或调节因子的自身抗体被发现,并被确认为可以引起C3肾小球病的独立致病机制,如H因子,C3致肾炎因子等,这就为针对不同变异进行精准治疗提供了基础和方向。同样,原发性膜性肾病也有不同的发病机制,大多数是由抗磷脂酶A2受体抗体引起,也有少部分由罕见抗原如牛血清和中性肽链内切酶(endopeptidase)引起,见于新生儿型原发膜性肾病。而用于原发性膜性肾病IgG亚型分类染色还同时帮助我们发现了其他新的肾脏疾病:如单克隆增殖性肾小球肾炎和IgG4相关性肾间质性肾炎。
激光微切割技术合并质谱分析在肾淀粉样变的鉴别中已常规应用。除去常见的可以用免疫荧光或免疫组化分析诊断的免疫球蛋白轻链,重链和血清淀粉样蛋白A(serum amyloid A)沉积物,这项技术帮助我们发现很多罕见的致肾淀粉样变的蛋白:如白细胞趋化因子,纤维蛋白原a链,载脂蛋白A-1和A-4,甲状腺结合前蛋白,凝溶胶蛋白,β2-微球蛋白等。蛋白质谱分析目前是分辨淀粉样变中不同致病分子的主要工具,对于确诊后的遗传咨询,治疗和预后等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生物分子研究对进一步理解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FSGS)的发病机制也有突破性的推动作用。除去形态学上的相似性,FSGS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各种基因变异而引发的不同足细胞病变。最初对nephrin,podocin,和WT1分子的识别是通过早期分子技术,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后期高通量二代测序技术有效地检出更多更复杂的基因变异。对于其他遗传性肾病如Alport综合征和遗传性囊性肾病,二代测序技术会更加高效地提供诊断与治疗的分子依据。
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人类基因组工程的顺利完成,生物研究的重心也逐渐由对单个基因或蛋白的关注,扩展到对某一特定生理状态下群组基因或蛋白变化的探测。基因芯片的蓬勃兴起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各种疾病的分子表型资料。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的基因表达对应于不同的组织病理形态与所处生理阶段都可以找到可循的分子模式变化。基因组在特定条件下表达数倍增高或减低可提供未知基因作用的线索;反之,已知功能基因的变化也可辅助判别生理病理过程。在肾病学科方面此类研究大多集中于肾移植活检。在关于移植器官的预后,细胞或体液免疫排斥,多瘤病毒(polyomavirus)肾病和慢性肾移植损伤的诊断等方面,已发现不少的特异基因标志物。例如在肾移植免疫排斥的诊断中,由抗体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引起的内皮特异分子的高表达,如第8因子,CD31,钙黏蛋白等,已被纳入Banff体液免疫排斥的诊断标准之一。在原发或遗传肾脏病方面,多囊肾病、急性肾损伤和原发肾小球肾炎的基因芯片研究也取得了很多进展。
分子诊断技术用于临床诊断的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在于对取材的要求。基因芯片和反转录PCR都需要新鲜组织,这就增加了取材的复杂性、风险和费用。而后兴起的NanoString nCounter计量分析系统可用石蜡包埋组织直接对感兴趣的分子进行计量分析。这项技术意味着分子分析资料可以直接与组织学形态挂钩,比如某些基因常在某种特定细胞中有高表达,这样通过直接的显微镜组织学检查,我们就可以知道分子表型材料的来源,是肾皮质还是髓质等,以协助诊断;这还意味着我们可以做到对大量的肾活检石蜡包埋组织档案再次取材进行回顾性分子表型研究,这样就为我们对各种肾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行性操作。最近单细胞RNA测序技术也已被尝试应用于正常组织功能及疾病分析,更是为深入了解肾脏细胞分类功能及疾病发生的原理与诊断提供了巨大的潜能。
如同任何一种病理检测手段,分子表型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并不一定具有疾病特异性,也就是说同样的分子表型模式会在不同肾病中出现重叠。例如不同病因导致的慢性晚期肾病阶段,分子表型模式极为相似,完全无法区分病因。因此,分子生物学诊断并不能取代现有的病理诊断方法,而只有通过与其他各种临床检测手段相结合,才能做到更好地为病患服务。
六、数字病理
在信息管理飞速发展并渗透到各行各业的今天,依靠计算机与数据方式管理病理图像,存储调动分析病理资料,正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字病理。数字病理是目前病理学界另一个飞速发展的全新领域。数字病理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在波士顿的Logan机场几张病理切片被转化为黑白数字图像并传输到麻省总医院。这个尝试得益于当时麻省总医院与某公司合作的一个软件编程项目。但由于当时计算机硬件及软件技术极不成熟,数字病理在20世纪70、80年代并无任何进步。直到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万维网的产生和应用,数字病理的可预见的巨大潜能才又重新开始提起人们的兴趣。由于数字病理的计算机性质,几乎无限可能地赋予这一领域的技术可调控性,数字病理将在远程诊断、教学、科研、会诊,甚至日常诊断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关数字病理的具体原理及各方面的应用优势,请参阅本书第94章数字肾脏病理学。
七、后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宋教育家及诗人朱熹借助池塘清澈因活水源源不断注入的现象,告诫后人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才能保持思想的活跃与进步。肾脏病理的未来对每个肾脏病理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不断接纳吸收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挑战。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肾脏病理将成为融合传统的形态学、免疫病理、血清学、临床表现、遗传、分子生物和信息科技为一体的学科,从而达到对疾病机制的更深入更精确的理解,迎接日益增长的精准诊疗时代的需求。肾脏病理同仁们,大家准备好了吗?
(刘 凛 周新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