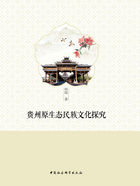
一 生态文化的研究
弄清生态文化的含义,是从理论上研究和实践上探索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生态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当然具有文化所具有的属性,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生态文化还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即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生态价值观。生态文化是人类的文化积淀,是由一定地区的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民间原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要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的结构和功用的文化体系,是代代因循沿袭下来的针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以及保护,它是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是可持续发展的学问和经验等文化的沉淀。
(一)国外有关生态文化问题研究的理论积淀
国际上对生态文化问题的研究偏重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最初的生态文化学是作为人类学的一个研究范畴出现的,它主要探究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上半叶,许多美国早期重要的人类学家如弗兰兹·博厄斯、克罗伯都精通欧洲和美国的哲学传统,并且深受进化论、功能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同时,它受多种思潮的影响,如“超级有机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播。当他们研究北美洲土著人时,他们经过仔细思考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文化区”,或“决定论”,以为环境直接决定着文化,即认为环境可以决定文化,为生态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途径。他们是生态文化学的先驱。1955年克罗伯的学生、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发表了他的《文化变迁理论》,阐述了生态文化的基本概念,这本专著的出版被广泛认为是生态文化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斯图尔德认为,文化与其生态环境是不可分开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他还认为,环境适应的概念构成了生态文化学之根蒂,近似的生态环境下会孕育产生近似的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线索,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培育了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线索的不同。由于世界上各种生态环境的存在,从而形成了世界的各种文化形态及其演化路径。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斯图尔德的影响,有三个重要的生态和文化方面的专著,即1968年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还有1969年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相继问世。20世纪70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演化进行了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认为技艺、经济因素是形成一个社会特质最基本的角色。哈里斯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是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是由娱乐和美学的产品和服务组成的。这些生态文化研究的成果,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生态文化学已基本成熟,影响范围也相应扩大,从美国人类学家的狭窄范围扩大到全球和多学科领域。而今,生态文化学家的分布改变了多年来以美国学者为中心的景况,逐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不但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加入了研究者的行列,并且其他地区的学者也积极参与或开展了关于生态文化学的研究。[1]
目前,除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外,一些工程学、传播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科研人员也纷纷参与到生态文化研究的队伍,20世纪末,国际上已显示出多国家和地区、多学科合作研究生态文化学的场景。
对国际上生态文化学的介绍,黄育馥发表了《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该文研究了文化生态的早期发展,主要探讨了斯图尔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并运用这一概念来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及采用的研究方法。[2]戢斗勇发表了《文化生态学论纲》一文,该文研究了文化生态学的定义,界定了其内涵和外延,认为文化生态学应研究文化系统、文化环境、文化资源、文化状况、文化规律;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的学科特点,界定了文化生态学是以生态学为方法的文化学,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是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兴学科;探讨了文化生态学的任务;等等。[3]
(二)当代中国生态文化问题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生态文化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偏重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忽视理论体系的构建,尤其是“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的概念混淆,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当然,笔者也不例外,本书中依然包含了这两个概念)。一般“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讨论的内容大体一致。从理论的应用来说,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自然环境的变化是早期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由于早期人类对自然环境能力的有限性,因此有必要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纠正,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而现在的人不是简单被动地适应环境,文化发展的实际过程,并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人类以满足他们自己更高的需求的本性。此外,如果扩大文化人类学来了解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受人类身心现象的影响,民族特性、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对人类自然环境的决定和支配,就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因此对文化生态的把握应该有更加宽广的视野。
目前,生态文化只是在一些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有介绍,关于生态文化的论文不多,也没有专著出版。
在国内生态文化的研究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必要研究其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作用,各自形成特定环境中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全球的自然条件是不同的,因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表达占据了全球的一部分。这种叠加在自然环境上的人类活动差别,反映到文化形态方面就会有差异性。它以人类自身创造出来,又受其感染、约束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来探究人类文化的发源和演变规律,比较各民族、各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造成的文化差异,研究其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它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提出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相关性,即研究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将文化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探究人的文化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其灵感是源自于自然生态中所交互的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对于文化生态学学科的定义、原理等方面的探究也有不少的论述,司马云杰提出:“文化生态学是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4]的观点。邓先瑞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5]潘艳、陈洪波认为:“文化生态学是就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6]王东昕认为:“文化生态学理论给予环境和文化充分的重视并强调了文化自身及环境发展的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7]梁渭雄、叶金宝认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理论,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一切因素,大体上包括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如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自然地理状况等;内环境是指文化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文化,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学派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等。”[8]管宁认为:所谓文化生态,是指就某一区域范围中,受某种文化特质的影响,文化的诸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所呈现出的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现实人文状况。[9]罗曼、马李辉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是由特定民族或特定地区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维护人类与自然界共存的共同利益,使人口、环境和资源良性循环的文化体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