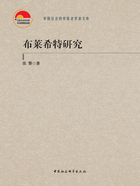
二 理解布莱希特的一把钥匙
布莱希特流亡美国期间,经德国导演艾尔文·皮斯卡托介绍,结识了中国留美作家蒋希曾(1899—1971)。他是布莱希特在美期间朋友圈子里唯一的中国人。有一天,蒋希曾邀请布莱希特和他的夫人看戏,两出“并不算短”的独幕剧,剧本是他自己编写的,还亲自参加了演出。时间是在1943年7月9日。蒋希曾用英文写过小说、诗歌和剧本,在美国一家专门为各国流亡者创办的“新社会研究所”戏剧部,师从皮斯卡托学习过演戏,当时已经加盟好莱坞当演员,所以布莱希特在当天的日记里称他为“中国作家和演员”。看完演出,三人聚在一起讨论了一阵戏剧表演艺术问题。蒋希曾是布莱希特史诗剧的崇拜者,第一次见面,他就以赞扬的口吻称布莱希特为“史诗剧创始人”。这个称呼大大出乎布莱希特的意料,因为自他创立史诗剧以来,在西方世界听见的大多是质疑之声,不少人无法理解,“史诗”与“戏剧”如何融合在一起。蒋希曾却不受西方艺术教条束缚,他是第一个用如此肯定的口吻称呼他的人,日后还在朋友圈子里为布莱希特的史诗剧进行过辩护。
其实,在布莱希特看来,蒋希曾未必完全理解他的史诗剧,与其说他推崇史诗剧,毋宁说他更推崇布莱希特其人。他从皮斯卡托那里得知,布莱希特在德国流亡者当中,虽然不是共产党人,却是个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他大概觉得布莱希特在这一点上是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他们在讨论表演艺术问题时,蒋希曾现场做了一番示范,以展示他对史诗剧表演艺术的理解。他手持一根木棒表演中国演员如何把它想象成一支枪。在他看来,这种虚拟的表演方式,与布莱希特史诗剧表演方式是一致的。可布莱希特却认为,他的表演不同于梅兰芳的表演,他运用的仍然是斯坦尼式“幻觉”技巧,而布莱希特更心仪梅兰芳式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不过蒋希曾对待史诗剧的态度,委实令布莱希特兴奋异常,他觉得中国人似乎最能理解他的史诗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经萌发过来中国定居的念头,可他毕竟是个用德文写作的剧作家,他的观众主要还是在德国。
布莱希特之所以产生“中国人最能理解他的史诗剧”的想法,不是没有原因的,事实上他创立史诗剧,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戏剧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他于1935年在莫斯科观摩过梅兰芳的京剧演出。当时他正在那里筹备创办《德国流亡者》杂志,他的苏联朋友,作家特列季雅科夫是梅兰芳访苏演出的组织者之一,请他观看了演出,参加了梅兰芳学术报告会。事后他撰写了论京剧“陌生化效果”的论文,深入阐述了他的史诗剧表演艺术主张,完善了他的史诗剧表演艺术理论。流亡美国期间,他趁在纽约逗留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在一位留美华人陪伴下,几乎天天晚上去中国城一家广东剧院看戏,那里的舞台装饰、音乐伴奏、演员表演、观众反应、剧场气氛等,既令他感到新鲜,又觉得似曾相识。从审美情趣来说,有不少是符合他的艺术追求的,但他却未曾想到过。在欧洲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演出,他从未想到,原来戏是可以这样演的,观众是可以这样看戏的。那时他只是读过一些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元杂剧剧本,例如李行道的《灰阑记》、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张国宾的《相国寺公孙合汗衫》等,这些剧作日后都成了他史诗剧创作的蓝本。他的《四川好人》即脱胎于《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高加索灰阑记》一看剧名就知道它的蓝本;教育剧《例外与常规》采纳的就是《相国寺公孙合汗衫》陈虎“以怨报德”的故事框架。更重要的是他从这些剧本的阅读中找到了创立史诗剧的锁钥,为解决史诗剧剧本结构问题,发现了许多切实可用,却又与欧洲戏剧传统截然不同的方法。例如剧本开头或中间的“楔子”手法;人物登场时的“自报家门”手法;剧本结尾的“审案”和“题目正名”等手法;剧本中的“歌唱”成分和虽然波澜起伏,但却不讲究高潮的剧本结构手法,等等。这些来自元杂剧的剧本结构方法的运用,令西方戏剧行内人士和观众为之震惊、骇然,产生一种陌生感,它们打破了欧洲传统戏剧的金字塔结构,使剧本增强了史诗的叙事特点,剧作家摆脱了亚里士多德戏剧美学的束缚,获得了更多自由挥洒的空间,这给欧洲戏剧的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史诗剧在欧洲戏剧创新方面,树立了一个成功范例,为欧洲戏剧发展注入了活力。20世纪后半期的欧美戏剧家,接受他的启发而成功者有之,属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者亦不乏其人,这样的人大都先天不足,不是没有戏剧艺术天分,而是没有他那样的哲学素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艺术界和学术界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真正理解布莱希特的戏剧艺术,离不开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成了理解和阐释布莱希特戏剧(包括诗歌、散文和戏剧理论)必不可少的工具。布莱希特像18世纪的莱辛、席勒、歌德一样,被读者和学术界尊称为“作家—思想家”(Dichter-Denker)。德国人欣赏文学作品,不限于作家是否会讲故事,情节是否跌宕起伏,是否引人入胜,他们更看重作家有无思想家的潜质,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如何,其中是否具有发人深思的哲理。所以“思想家”是德国人衡量作家的最高标准。布莱希特被人称为思想家,除了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理解和运用。
布莱希特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恰值德国大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福克(Alfred Forke,1867—1944)等人,顶着“中国是木乃伊”“中国人是黄祸”的污蔑之风,纷纷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翻译成德文,介绍给德国读者的时候。这时也正是德国表现主义文艺思潮滥觞之际,不少表现主义作家成了中国古代哲学译著的热心读者,什么“无为”“无何有之乡”“人性善”等词汇,成了德国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借用中国哲学思想,表达对德国现实的认识,成了一种文坛风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德布林的长篇小说《王伦三跳》,作者借清末山东寿张农民起义的故事,演绎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小说主人公王伦从一个在社会上求生存的普通渔民,到一个宁愿做与世无争、逃避社会的弱者,最后被逼无奈,成了反抗社会的义军首领。起义遭到镇压而失败,最后作者借一位牺牲了两个儿子的母亲之口提出:“沉默,不反抗,我能做得到吗?”这样的自问,实际上是作者在描写了王伦的人生三个阶段之后,提出了赞成还是反对暴力革命的问题。用当时的话说:做个“无为”之人,还是做个“行动”之人。当时有一份著名杂志就叫《行动》(Aktion)。莱昂哈特·弗兰克的一本小说集甚至冠以《人性善》(Der Mensch ist gut)的书名,为此作者常常遭到人们的讪笑,有人讽刺说:“德国人就是有当哲学教授的癖好”,还有人用揶揄的口吻说:“人性善,小牛肉香”,意思是说相信“人性善”的人,可能会像小牛一样,成为人家餐桌上的美食。德国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由于表现主义是诗歌的天下,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几乎占了这股“中国文化热”的半壁江山,一时之间出现了许多中国诗歌翻译家,如汉斯·贝特阁、奥托·豪赛尔、阿尔伯特·艾伦斯坦、汉斯·海勒曼、克拉崩等。克拉崩还把《灰阑记》改编成一出同名童话剧,它的演出不仅对20世纪上半期德国戏剧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而且最先启发了布莱希特创立史诗剧的欲望,他从中国元杂剧的某些范本,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改革欧洲戏剧的方向。布莱希特虽然并不属于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甚至对表现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毕竟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在这个大气候里开始了文学创作,“中国文化热”必然也波及他。
现在大家都知道,20世纪20年代中期,布莱希特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在广泛阅读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德文译本。从他作品透露的信息可以判断,他阅读过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墨子》、孔子的《论语》、《孟子》、《列子》、《孙子兵法》、《易经》、《吕氏春秋》等著作,甚至还读过《尚书》和西方人写的“中国思想史”一类著作。据他的合作者、作曲家汉斯·艾斯勒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们开始合作的时候,布莱希特曾经把自己手头阿尔弗雷德·福克翻译的《墨子》推荐给他阅读,这本书被他们视为人生的“重大发现”。据他观察,布莱希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从中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汲取“思想启发”(Denkanregung)。布莱希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他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有惊人的记忆力。这一点颇似我国大学者钱锺书。只不过,他读书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像艾斯勒说的那样,是为他的文学创作汲取“思想启发”。他从未像小说家黑塞那样关心过《易经》的卜筮操作方法,也从未像汉学家卫礼贤那样,在朋友圈子里表演卜筮过程,以展示《易经》的神秘性。
布莱希特对这些著作中的新语言、新思想、新的表达方式极为敏感,它们常常会成为他进行文学思维,改革艺术表达方式,塑造人物形象的动力。以《易经》为例,“师挂”“遁卦”“明夷卦”所阐释的道理,令流亡中的布莱希特茅塞顿开,使他认识到,法西斯恶势力当道,光明受到损伤,反法西斯主义者就应该懂得“以退为进”“身退道不退”“韬光养晦”,把弱势转化为优势的斗争策略。这些道理给布莱希特以非同寻常的启发。他在流亡途中创作的教育剧《贺拉提人和库里亚提人》,以中国“武戏”的形式,表现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退为进,避实击虚,出奇兵反败为胜的辩证法。《伽利略传》则塑造了一个“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的周文王式的天文学家形象,他在软禁期间完成《两种科学体系的对话》,令人想到周文王囚羑里演周易的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则塑造了一个“佯狂披发,以晦其明”的箕子式帅克形象。不甚了解这些形象来源的学者,还以为布莱希特凭空开创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呢。其实,它们都是布莱希特在《易经》的启发下而进行的艺术创造。他在流亡芬兰期间创作对话体散文《逃亡者对话》,这个标题显然也是受“遁卦”这个卦名的启发而命名的。他在流亡途中撰写的那些中国哲学笔记式散文,最初就是命名为《易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者和出版家把它们编辑在一起时,才命名为《墨子/易经》,这是因为这些小故事的主人公大都称为“墨子”。遗憾的是,布莱希特与《易经》的关系这个课题,至今在国际布莱希特学界还是个空白。这显然与《易经》太难读懂有关系。中国人都把它视为“天书”,外国人就更是敬而远之了。布莱希特却能从中汲取“思想启发”,创作出一系列文学作品,不啻为惊人之举。
又例如作者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借性格各异的母子四人的不同遭遇,艺术地演绎了《庄子·盗趾》中满苟得对“忠信廉义”的批判。剧中的大胆妈妈本想率领一家人靠战争讨生活,结果却是大儿子死于勇敢,二儿子死于诚实,小女儿死于善良,她自己则由于过分精明算计,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故事表现了欲在战争中捞取好处,必然自取灭亡的主题。这个思想出自《庄子·列御寇》:有德之人绝不强求别人之物,故不会兵戎相见;无德之人总是强求别人之物,故容易刀兵相见。追随战争的人,是想在战争中捞取好处,而欲借战争发财的人,必然自取灭亡。剧本最初上演时,一些缺乏中国哲学知识的行内人士,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作者为何要这样处理大胆妈妈一家人的结局,曾经引发了热烈讨论。读者在《高加索灰阑记》的格鲁雪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可以感受作者对墨子“兼爱”思想的演绎,在阿兹达克身上可以体会墨子的“侠义”精神,剧本的“楔子”和全剧的结尾,则演绎了墨子的“实用”主张。读者如果对墨子的“断指存腕”(“大取”第四十四)思想有所了解,一定会更深刻理解教育剧《措施》的主题思想,而不会像某些对共产主义运动抱有偏见的人那样,把它解释成“共产党人不讲人性”。其实这里表现的是在生死问题上“权衡利弊”问题,即墨子所说“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生死的价值问题,或曰如何对待革命的牺牲精神问题。布莱希特在教育剧《说是的人》中,借一出日本“能剧”故事也讨论过同样问题。所以二战以后,当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就《措施》描写的内容而怀疑他是共产党人时,他回答说:它与《说是的人》讨论的是同样问题。这个回答让既不懂布莱希特戏剧艺术,又对中国哲学一无所知的审讯者顿时语塞。
布莱希特的剧本里,自然也包括他的诗歌、散文,几乎处处散落着中国古代哲人智慧的亮点,像天空的繁星一般,如果你没有一双中国古代哲学的眼睛,你也无法识别它们,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那样闪烁,那样耀眼,那样发人深思。这是他的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老子关于水的品质的赞颂,被布莱希特用在《老子流亡途中著“道德经”的传说》这首诗里,表达反法西斯斗争必胜的信念;用在《圆头党和尖头党》剧本里,表达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用在《城市丛林》剧本里,表现事物在普遍规律之外,也有特殊存在状态的可能性;有时给朋友写一纸祝寿的贺词,写一封普通信件,他也要让老子代替自己说话。一首翻译成汉语不到二十个字的短诗《墓志铭》,采用的是庄子师徒讨论丧葬问题的表达方式。另一首标题为《题一座中国茶树根雕狮子》的短诗,开头两行:“坏人惧怕你的利爪,好人喜欢你的优美”,套用的是《列子·杨朱篇》中描述“子产相郑”取得突出成就的两句话:“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三毛钱歌剧》里最著名的一句台词“先填饱肚子,然后再讲道德”,它的来源是孟子关于财产与道德关系的议论;其中的《所罗门之歌》洋溢着历史辩证法思想,显然是老子《道德经》第18章的戏仿之作,等等。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你发现得越多,你对布莱希特作品的理解越深,你就越懂得,为什么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众口一词,称誉他为“作家—思想家”。
可惜,我国布莱希特研究,时至今日,在这个领域,几乎还是空白,远远落后于我们的邻国韩国的日耳曼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学者金崇德(Kim Tschong-Dae)、宋云耀(Song Yun-Yeop)、尹寒松(Yim Han-Soon)等人,凭着他们良好的汉学基础,撰写了关于布莱希特与中国哲学的博士论文,为人们深入理解布莱希特的作品开创了新局面,推动布莱希特研究走向新天地,达到新水平。它们提醒读者,特别是学术界同仁,解读布莱希特,离不开中国古代哲学,它是打开布莱希特这个百宝箱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但愿我国布莱希特研究,更多关注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更多发现布莱希特作品的新气象,使我们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让我国读者对布莱希特作品的审美眼光更为开阔,更为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