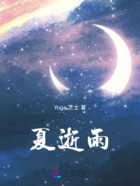
第6章
高考前的冬天格外漫长。
我和L的视频窗口成了深夜唯一的慰藉,屏幕里的她总是裹着厚厚的珊瑚绒睡衣,台灯在她脸上投下温暖的橘色光晕。
我们隔着像素点组成的画面同步刷题,偶尔抬头相视一笑,耳机里传来彼此翻动卷子的沙沙声。
“这道导数题...”某个凌晨两点,我的声音已经哑得不成样子。
L突然举起笔记本,上面画着夸张的哭脸:“去他的数学,我要睡觉!”
我们对着屏幕大笑,笑着笑着却都红了眼眶。
窗外飘着那年第一场雪,落在摄像头前像一场微型暴风雪。
二月最冷的那天,L的头像突然灰了。
她妈妈用她的账号发来消息:“手机没收,高考前禁网。”
我的世界突然安静得可怕,台灯的光线变得刺眼,草稿纸上还留着我们昨晚讨论的数列题,铅笔痕迹像一串孤独的密码。
补习班的偶遇像是命运开的玩笑。
推开教室门看见L的瞬间,我手里的奶茶差点打翻。
她瘦了不少,马尾辫扎得更紧了,额头上冒着一颗压力痘。
我们隔着三排座位,却能通过后背的弧度判断对方的状态——L卡壳时会不自觉地揪后颈的碎发,而我习惯用自动铅笔戳太阳穴。
高考结束那天的夕阳特别美。我和L坐在空荡荡的操场上,把复习资料折成纸飞机扔向天空。
她的第一志愿是BJ那所985的王牌专业,我的目标则是同城的211。
“大不了每周坐高铁找你。”L把冰镇可乐贴在我脸上,水珠顺着下巴滴在校服领口,像一颗小小的流星。
查分那天,601.5这个数字在我眼前跳动。
L在电话那头轻轻倒吸一口气:“我...622。”
我们沉默了很久,听筒里只有彼此的呼吸声。
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很响,像某种倒计时。
0.5分的差距,在志愿系统里不过是一个数字的差别,却像宇宙中两颗相邻的星辰——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亿万光年。
L突然发来视频请求。
凌晨两点十七分,她的脸在手机屏幕里泛着蓝光,身后的行李箱大敞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洗漱包、折叠衣架、防潮袋装好的羽绒服。
“我点了确认。”她的声音像一片雪花落在手背上,“BJ那所。”
我的鼠标悬在“提交”按钮上,汗液在掌心与塑料之间形成黏腻的薄膜。
突然想起小学毕业那天,她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一颗玻璃珠,说:“对着阳光看,里面有整个银河系。”
此刻我的电脑屏幕也映着星光——是去年冬天和L在天文台拍的星轨照片,她指着猎户座说:“你看,这三颗连起来像不像我们?”
母亲撞开房门时,我正在撕录取通知书的快递袋。
“体育专业?!”她的手掌拍在玻璃茶几上,果盘里的砂糖橘跟着跳了跳。
“你知不知道隔壁陈阿姨女儿保送复旦了?楼上的明明哥拿了港大奖学金?”
她的指甲陷进我小臂的皮肤里,像要剜掉那块写着…的旧伤疤。
我盯着茶几上渐渐融化的冰镇可乐,突然发现自己的眼泪正一滴滴砸在“运动训练”四个烫金大字上。
母亲的手突然松开了。
“坏孩子...”她跌坐在沙发里,这三个字轻得像一声叹息,却让我如坠冰窟。
后来我在储物柜最深处找到了那颗玻璃珠。
对着台灯看的时候,终于明白L当年没说完的话——那些折射的光点不是星空,是我们在不同轨道运行的人生。
就像现在,她的航班即将掠过平流层,而我的跑鞋正深深陷进煤渣跑道里。
BJ和上海之间,隔着的从来不只是0.5分。
L的微信提示音在深夜里格外清晰,一条接一条地亮起屏幕。
最后一条跳出时,我的手机微微震动:“我买了明天的车票,我们去看海吧。”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银色的细线,像是银河为我们指引方向。
我盯着那道光线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凌晨四点,我悄悄拧开门锁,生怕惊动沉睡中的房子。
餐桌上放着一碗冰镇绿豆汤,表面结着细密的水珠。
旁边压着一张字条,母亲的笔迹有些潦草:“防暑的。”
我端起碗一饮而尽,甜味里带着一丝微苦,就像这些年咽下的所有遗憾。
海边日出前,我和L赤脚站在沙滩上等待。
潮水涌来时,L的帆布鞋里灌满了沙子,她索性把鞋子甩到一边,大笑着拉起我的手冲向浪花。
“快看!”她指着天际线。
朝霞像打翻的调色盘,把云层染成渐变的橘红色,从淡粉到金黄,最后融进靛蓝的海水里。
我们并肩站着,任凭冰凉的海水没过脚踝,打湿裤脚。
潮水退去时,L突然蹲下身,在湿漉漉的沙滩上写下“601.5”和“622”——那是我们高考分数的最后三位。
我看着她认真的侧脸被晨光镀上一层金边,睫毛在脸上投下细小的阴影。
“0.5分算什么。”她抬头冲我笑,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在大海面前,我们都是小数点。”
海浪温柔地漫上来,将那些数字一点点抚平。
我望着逐渐消失的痕迹,突然明白:有些距离看似无法跨越,却能在更广阔的尺度下变得微不足道。
回程的火车上,阳光透过车窗洒进来。
L背包上挂着的生肖吊坠一晃一晃的——那是小学毕业时我们互换的礼物,经过十年光阴,镀层已经有些剥落,却依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下次见面,” L把吊坠捏在手心里,“可能就是BJ和上海的距离了。”
我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轻声说:“没关系,潮水会带来,也会带走。”
就像那碗放在餐桌上的绿豆汤,就像沙滩上转瞬即逝的数字,就像我们之间永远存在的0.5分——有些东西看似被抹去,却早已刻进记忆的纹理里。
当列车穿过漫长的隧道时,我们的倒影在车窗上重叠。
黑暗中,生肖吊坠发出细微的碰撞声,像是跨越时空的回应。
————————————
体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餐桌上投下一片阴影。
我盯着“运动康复”四个字,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曾经用来解微积分题的茧——现在它们正在变成打排球磨出的硬皮。
书架上蒙尘的医学教材、抽屉里收集的各校法学院简介,全都成了上个世纪的遗物。
“你知道王阿姨的女儿保送北大医学院了吗?”母亲擦着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杯,水珠顺着杯壁滑落,像一串无声的眼泪。
“体育生...”她突然用力过猛,杯底在茶几上磕出清脆的裂响,“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第一堂体能训练课,我在四百米跑道吐了三次。
烈日把塑胶跑道烤出刺鼻的味道,汗水蛰得眼睛生疼。
教练的哨声像是催命符,我踉跄着跑在最后,耳边回荡着母亲那句“复读吧”,眼前却浮现L发来的信息:“我在图书馆发现本《运动解剖学》,你要不要?”
深夜的浴室里,我盯着镜中陌生的自己:晒得黝黑的皮肤,肩膀上磨破的水泡,右膝上狰狞的淤青。
热水冲下来时,我忽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不是因为这身伤,而是发现书桌抽屉里那沓医学院简介,不知何时被母亲换成了运动防护指南。
转折发生在深秋的校际联赛。
我作为替补上场时,看台上空荡荡的只有零星几个观众。
第三局关键时刻,那个救球动作完全是本能——我飞身扑向边线,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却把球救了起来。
掌声响起时,我才发现掌心火辣辣地疼,塑胶颗粒嵌在血肉里,像撒了把星星。
赛后更衣室里,教练扔给我一管药膏:“运动康复专业就缺你这种有实战经验的。”
药膏薄荷味刺鼻,我却突然想起小时候发烧,太太用生姜片给我擦背的灼热感。
窗外飘来桂花香,恍惚间仿佛听见她说:“要笑啊。”
我开始在图书馆角落啃专业书籍,那些肌肉图谱渐渐变得亲切起来。
有次在解剖室对照模型找肌腱位置,抬头发现窗外站着母亲。
她手里拎着保温桶,眼神复杂地看着我面前摊开的《运动损伤学》。
我们隔着一层玻璃对视,最后她轻轻放下保温桶转身离去——里面装着以前最讨厌的胡萝卜排骨汤,现在却成了训练后最好的补给。
省级比赛夺冠那天,颁奖台后的LED屏突然播放起我的救球集锦。
看台上有个熟悉的身影倏地站起来,是母亲举着手机在录像,镜头反光晃到了我的眼睛。
回校的大巴上,L发来张照片:我小时候穿着 oversized白大褂玩医生的模样,旁边P上了现在穿运动服领奖的身影。
“看,”她写道,“你一直在治愈别人,只是方式不同。”
车窗外的夕阳把云层烧成橘红色,我突然想起教练常说的话:人生就像打排球,重要的不是扣杀有多漂亮,而是永远能把接到的球传向最合适的位置。
现在我的书架上,医学教材旁边摆满了运动科学著作。
有时深夜复习到头晕眼花,就会摸一摸床头那个用绷带缠好的旧排球——那是初中第一次比赛时用的,上面还有太太绣的歪歪扭扭的名字。
线头已经有些松脱,但每次触碰,掌心仍会传来熟悉的温度,仿佛那些未完成的梦想,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
领奖台的镁光灯刺得我睁不开眼。
金牌挂在脖子上沉甸甸的,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队友们潮水般涌来拥抱时,我闻到了汗水、止汗露和眼泪混合的咸腥味。
队长把冰镇矿泉水浇在我头上,凉意顺着脊椎流下,我才终于确信这不是梦境——我们真的赢了。
庆功宴持续到凌晨。
KTV里,平时严肃的教练正用跑调的嗓音吼着《真心英雄》,替补队员把奶油蛋糕抹在我脸上,甜腻的触感让我想起小时候太太奖励的棉花糖。
回宿舍的路上,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不知是谁起了头,我们突然在空旷的街道上开始传球,笑声惊醒了路边的麻雀。
但冠军的光环褪色得比想象中更快。
新赛季的对手名单上,赫然印着去年全国亚军队伍的名字。
晨训时间提前到五点,寒冬的操场呵气成霜。
我拖着酸痛的双腿完成第二十组折返跑时,胃里突然翻涌起铁锈味——是牙龈不知何时咬出了血。
二月最冷的那天,我在浴室发现体温计显示38.5℃。镜
中的自己面色潮红,眼下挂着两轮青黑。
“只是感冒。”我吞下两片退烧药,把体温计塞回抽屉最里层。
训练时每个扣球动作都像在撕裂肌肉,但我不敢停下——替补席上学妹热切的目光像无形的鞭子。
比赛前夜,我在宿舍床上辗转反侧。
手机屏幕亮起,是L发来的消息:“明天我会在第三排看台。”
配图是我们初中时第一次比赛的合影,照片里我正狼狈地扑救,而她抓拍的瞬间,球刚好停在距地面一厘米的位置。
决赛日阳光毒辣。
下车时热浪扑面而来,眼前的台阶突然扭曲成波浪状。
耳鸣声中,我听见队长在喊我的名字,声音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膝盖接触到地面的瞬间,塑胶跑道灼热的温度透过布料传来——奇怪的是并不觉得疼,反而有种终于可以休息的解脱感。
医院天花板的白炽灯刺得眼睛生疼。
输液管里的点滴声里,我听见医生对教练说:“39.8℃,再晚点送来可能引发心肌炎。”
病床边的柜子上摆着队友们送的水果,最上面那苹果贴着便签:“队长说这次换我们救你的球。”
高烧退去的第四天,母亲突然出现在病房。
她放下保温桶的动作很重,汤却一滴没洒。
“从小就这样,”她拧毛巾给我擦脸,“发烧就装没事人。”
毛巾上有熟悉的洗衣粉味道,是小时候发烧时她总用来给我物理降温的那款。
窗外暮色渐沉,我们谁都没提比赛结果。
养病期间,L寄来一箱书。
最上面那本《运动员心理建设》里夹着张字条:“你扑救的样子,一直是我见过最美的抛物线。”
午后阳光里,我开始认真翻阅这些曾被我视为“退而求其次”的专业书籍,发现运动康复学的解剖图,竟和当年珍藏的医学教材如此相似。
归队那天正值春末。
更衣室里,我的柜子被学妹们贴满便签。
训练场上,教练吹响集合哨:“今天练保护性跌倒。”
他示范动作时,护膝与地面摩擦发出熟悉的声响。
我深吸一口气,助跑、起跳、落地翻滚——塑胶颗粒沾满手臂的触感,莫名让人眼眶发热。
赛季最后一场比赛,我们止步省八强。
谢幕时,看台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抬头望向第三排座位,L正举着当年少年宫相遇时我送她的卡通加油牌。
阳光下,她手腕上的生肖吊坠闪闪发亮,像一颗永不坠落的星辰。
回程大巴上,教练播放比赛录像。
放到那个鱼跃救球镜头时,后排学妹突然小声惊呼:“师姐动作好像教科书啊!”
全车哄笑中,我望向窗外飞逝的景色,突然明白:人生不是冲刺跑,而是接力赛——有时候接过别人递来的接力棒,也能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赛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