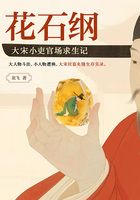
第3章 两难抉择
李素一进红江县,先听到的便是朱县令的死讯。
他只怕是自己听错了,急忙又跟人细细地问,一来二去,李素才知道,他告假离开红江的第三日半夜,朱县令便猝死在县衙。
李素心中既惊,且悲,匆匆忙忙便赶到县衙,一进大门,先看到了快班衙役的班头陈二。
“李大人!您回来了?”陈二一见李素,躬身一揖,那神情语气,比李素告假之前又恭敬亲热了许多,脸上细密的皱纹绽放如菊,笑道,“原以为大人此次告假,总也要一月时间,不承想这才半月出头,大人便回来了,也是巧,城南的玉丰楼新来的厨子,今晚小的们做东,给大人接风……”
“这些都好说,陈班头,我刚到县里,听人说,咱们朱大人……”
“朱大人啊……急病,没了,也就是十多天前的事。”
“那朱大人的后事?”李素急切追问道,“大人的灵柩,如今何在?”
“过了头七,朱夫人带着儿女,扶灵归乡了。”
“已经……已经走了?”
“朱大人过世,朱夫人家里人仍住在衙门后堂,其实……也不妥当。”
朱县令为官严苛,却也清廉,是个一清到底的官。他在红江任上两年多时间,不仅自己不取一文赃钱,就连衙门里的大小属员,也都不许收受贿赂。
如此一来,便等于断了衙门里那帮人的财路,众人心里愤恨,却不敢明言。
朱县令过世之后,朱夫人知道自己丈夫平素里得罪的人多,也不想多做停留,和自己的儿女一起,送朱县令的灵柩回老家去。
李素只觉得心中难过,他到红江做县丞,朱县令始终对他不薄。红江县算是大县,县丞这个位置只是八品前程,却不知有多少人眼热。
顺安府那边曾经两次要安插人来顶替李素,再将李素平调至岭南,都被朱县令硬顶了回去。
若非朱县令,此时的李素,只怕已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了。
“李大人,李大人?”陈二见李素走神,轻轻唤了他一声,又赔着笑脸说道,“今日这接风酒,大人务必赏脸,朱县令病故,如今这衙门里大小事务,便都着落在大人身上,小的们少不得要仰仗大人……”
“回头再说,再说……”
李素一路劳顿,此刻走起路也觉得两脚虚浮,他进了衙门大门,心中愈发不是滋味。
朱县令清廉,一家老小吃喝用度,外加衙门里几名师爷小吏的薪酬,全是从自己俸禄里支取的,每年下来,只勉强不落亏空而已,决计攒不下一文钱。朱县令的家人此时扶灵回乡,境遇不定有多么窘迫。
李素咬了咬牙,他回乡迁坟,便已支了十贯钱,几近两月的俸禄,再加上先前欠下的账,肩上的担子更重,可他总是不忍,立刻又从公使钱中支了十贯。
朱家人扶灵而归,必然也走不快,李素派人骑了衙门马厩里唯一的一匹老马,务必追上朱家人,将那十贯钱送上。
朱县令故去,红江县县衙正堂的位置,暂时空缺,上峰重新委派官员来接任,也不是三五日便可办妥的,最快也要两三个月,有时拖上五六个月也是常事。
按照惯例,正堂出缺,便由县丞权知县事。好在朱县令先前调配有方,衙门里那些人各司其职,若不是出了什么大事情,都应付得来。李素在县衙里主持了两日,一切顺利。
他孤身一人在红江做官,也不摆什么排场,平日就住在衙门的值房内,也可省却一笔租赁宅院的开销。夜深人静时,李素小心翼翼取出那块自祖坟中无意得到的琥珀,借着油灯的光,细细观看。
琥珀已经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火光映照之下,琥珀散发着一团淡淡的润光,其中那四个由松针拼凑出来的字,也愈发清晰。
这块琥珀虽不能说巧夺天工,却也珍稀到了极点,尤其琥珀内“天下太平”那四个字,绝然是造化所酝,李素平日并不喜这些物事,可轻轻抚摸着这块琥珀,也觉得爱不释手。
他把玩了片刻,将琥珀装入匣中,又放回到身后的柜子里,待重新坐下时,李素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若朱县令还活着,此事却也好办,李素只需呈上琥珀,其余事务,便都该由朱县令主持。
可如今朱县令病故,李素暂管县事,这差事绕了一圈,又落回到他身上。
有些事情,李素先前未曾想过,但此刻却由不得他不去斟酌。
对李素而言,进奉花石纲,有两条路可走。
头一条路,便是按照先前所想,从红江县上报至顺安府,再由顺安府上报京师。这是按部就班的一条路径,合乎规程。
第二条路,则算是一条捷径。苏州的应奉局,专管江南花石纲,有些人进奉花石纲,想要取巧,便会绕开自己的顶头上司,径直把东西送往应奉局。
江南官场皆知,应奉局的首脑朱勔豪奢,对进奉花石纲的官员,从不吝惜财物,只要东西送至应奉局,无论将来京师那边有多少封赏,朱勔这里便先给一笔钱,至少也是五百贯起步。
若东西呈送京师之后,上头有了旨意,朱勔也不贪他人之功,对进献者刻意提拔,正因此,江南半个官场的官,都出自朱勔门下。
此时此刻,李素自然也有自己的心思。
若朱县令在任,李素信得过,朱县令君子心性,绝不会平白就贪了李素的功劳。
若朱县令不在,李素对顺安府的那些人,便没有多少信任可言,他好歹也是官场上的人,深知这汪水有多深多黑。
到底该何去何从?
李素只觉得难以决断,忍不住就在屋中来回踱步,他本是个循规蹈矩之人,又在朱县令这种人手下做了两年差事,心中实在生不出非分之想。
可转念间,李素又想到如今的处境,一家老小都指望着自己,再加上欠下的债,李素只想一想,便觉得头大如斗。
若从应奉局那里得了五百贯,所有外账,立刻就能还清,结余下来的,还够在家乡再多买几十亩田,雇人去种,家里只管收租,如此,日子便好过得多了。
若朝廷那边还能再下一些赏赐,更是锦上添花,不敢说就此平步青云,但从此之后,在家乡那边,李素无疑便是人上人。
李素想了半夜,第二日起身后,一边料理衙门里的公务,一边仍在想,却始终做不出决断。
等到公务忙完,已是到了申时中,李素微微觉得肚饿,刚打算到衙门后厨去找些吃食,却突然想起一个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