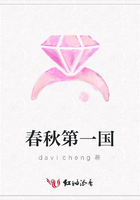
第2章 燮父迁都改唐为晋 文侯勤王以臣定君
唐侯叔虞薨后,康王准世子燮父继为唐侯,年方一十五岁,因见唐城地狭不平,交通不便,宫室卑矮,难以御外治内,于是对群臣说道:“今唐城地处狭谷,道路不平,致先侯倾复归天,孤甚恶之。又宫室卑小,形制粗鄙,不足以成壮观、畏戎狄,孤想在平广之地另建一城,把社稷宗庙迁到那里,众卿以为如何?”司空出班奏道:“吾君所言甚是,唐城地狭民稀,非建都之地。臣见晋水入浍之处,地甚平坦开阔,且先侯所兴水利,有舟楫灌溉之便,是新都的绝佳之选。”燮父大喜,择日亲至浍水河边,主持开工大典,发工匠民夫营建新都,五年后建成,因城东山形,如鸟舒翼,故名新都曰翼(今翼城县天马村)。
燮父斋戒数日,使祝史作文,将迁都缘由,祭告宗庙,择吉迁翼,见宫室宽广,飞檐挑梁,形制宏伟,铃铎声闻数里,心中甚喜,对左右说道:“孤今日方为一国之君,往日不过是一个富家郎罢了。”左右皆贺。燮父又对群臣说:“唐乃是尧陶旧国,因助武庚叛乱,被我先王所灭,岂可复用其国号,以淆视听,今既已迁都,不如再改国号,怎样?”群臣附和道:“国号当改,但不知改为何名为妥?”燮父指着宫外晋水说道:“翼都之旁有晋水,晋的意思,是君子自昭明德之意,且晋,亚日也,明出地上,喻国势蒸蒸日上,如日之在天,以此为国号,再好不过了。”众人皆无异议,于是再告宗庙,又驰书报周天子,遍告各国,国号改唐为晋,燮父自称晋侯,晋之名号,自此始有,这是周康王九年的事。
晋侯一日到后宫来见母后,宋太后说道:“我儿少年即位,能继承父志,带领群臣,治理一国之民,我心很感安慰,只是我儿年已弱冠,后宫尚空,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这事呢?”晋侯慷慨激昂地说道:“现在晋国周围,群敌环伺,国内人心不稳,戎狄未定,何以家为?”宋太后高兴地说:“我儿能有此大志,以国事为重,确实可嘉,但成夫妇之礼,继宗祧血脉,也是国君的大事,不可缺失。”晋侯说:“这事以后慢慢再说吧。”
再说那周康王见燮父没有奉诏而迁都并擅改国号,心中已是很不高兴,又听说翼城宫室宽广,大大超过诸侯的规定,几乎和王宫相当,心中更怒,于是派遣使者严厉斥责说:“大凡建立邦国,都要以土圭来测其地而筑其城,这是有一定的制度的,此先王所立,不可违背。昔日尧、舜在位,茅椽而土阶,禹居宫室卑小,他们都不以为陋。你说唐城宫室卑矮,无以服戎狄,今镐京的宫室还算可以,你来住吧!”晋侯见康王动怒,虽是十二分的不愿意,也只好迁回唐城原宫室居住,只宗庙、社稷不便再迁回,仍在翼城,四时亲来参拜祭祀。
晋侯燮父自宫室逾制受到康王批评之后,将那追求享乐、崇尚奢华之心收起,一心治国利民,不出几年,果然将晋国治理得物阜民安,日益强盛,戎狄不敢来犯,诸侯仰敬,天下人都知道晋侯燮父很能干。康王见晋国日益强大,燮父颇具人望,是王室可以倚靠之人,于是封为周室卿士,与鲁侯禽父、卫侯懋(音茂)父共同参与周朝事务,时人称为“三父”,都有贤名。
周康王二十五年,因荆楚不遵王化,僭(音见,超越本份)越称王,侵夺华夏诸国,康王就集合晋、齐、卫、郑等国,合兵车千乘,甲士五万,往讨楚国。楚地阴湿,阡陌未开,道路不通,不利车战。晋侯奏道:“臣军中有戎狄兵数千,惯行泥泞之路,登山如履平地,以这些人为前驱,兵车继后,楚兵不难胜也。”康王大喜,次日依言而行,果见那戎狄之兵,漫山遍野,不择道路,踏田而进,诸侯兵车随后数路齐发,楚军不能抵挡,楚王求和,愿意去掉王号,每年贡周王室菁茅一车。那菁茅本无甚大用,只供祭祀时缩酒之用,康王因荆楚久在化外,不通中原,只要肯臣服就行,并不计较贡物的多寡贵贱,所以同意罢兵息战。
康王二十八年,周康王为表扬燮父征楚之功,正式批准唐改国号为晋,准其入居新都翼。
晋侯自燮父之下,历史资料缺失,事迹均不可考,只知其名号和在位顺序,计有武侯(宁族)、成侯(服人)、厉侯(福)、靖侯(宜臼)、釐侯(司徒)、献侯(籍)、穆侯(弗生)诸世,都遵循其祖唐叔虞的统治方法和纲领,国力渐强,疆域日大,特别是穆侯在位时期,经常对外用兵,扩展国土。晋穆侯七年,公元前805年夏七月,又发兵车二百乘,士卒万人,往伐条戎(今运城附近鸣条岗一带),司马杜行父劝谏道:“方今天气溽热,我兵都是长期生长居住在高凉之处的人,进兵条戎,恐不胜其热,难以取胜,不如待九月秋凉后进兵,方可收预期之效。”穆侯说道:“现在军士们都已经集合起来了,如果改期,恐怕会影响士气。”于是不听劝谏,传令向条戎进发。时值盛夏,骄阳如火,士卒们顶盔贯甲,冒暑而行,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到得条戎地面,个个汗流浃背,已是师老兵疲,了无斗志了,怎当得那条戎之兵息于阴凉之处,以逸待劳,斗志正盛。两军相交,晋军很快不支,前军败退,反冲动后军,自相践踏,折兵大半,穆侯因不听司马之言而致败,心中很是郁闷,回到翼城,恨恨说道:“条戎之仇不报,誓不为君。”恰在此时,夫人姜氏生下一子,派内侍来请求起名,穆侯随口说道:“仇。”姜氏只怕内侍错听,再让来问,仍是同样回答,只好以仇为名,其后立为世子。
穆侯思报条戎兵败之仇,加紧操练兵马,整顿军备,想再去征讨,还没等到出发,北方边境守官来报:“北戎犯我边境,掳掠人民,毁我城郭,请君定夺。”穆侯怒道:“北戎欺我太甚,既来挑衅,当先灭此而后再报条戎之仇。”于是转而向北来伐北戎,穆侯十年,前802年,两军战于千亩(今安泽县北)。那晋军休整三年,兵气复振,又闻得北戎无故来犯,祸害我人民,皆欲报仇,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只杀得北戎兵七零八落,尸横遍野,戎王见不能敌,不得不弃城远遁。穆侯大获全胜,将那北戎全境收归晋国版图,设官理民,奏凯还朝。恰此时姜氏又产一子,穆侯大喜,为其取名“成师”,成师者,师出有成之意,又指能成其众也。大夫师服劝谏道:“命名应根据事物本身的意义来定,岂可凭主公一时的情绪来决定?愿主公认真考虑,还是改了吧。”穆侯说道:“二子之名,皆纪军国之大事,名与事正好相应,又何必改呢?卿不要再说了。”师服出而叹道:“世子和次子之名意思乖戾颠倒,世子恐怕要丢掉他的国家了。”
晋穆侯二十七年,前785年,穆侯薨,群臣议立世子仇继位,征求姜氏的意见,谁知姜氏受穆侯的影响,偏爱小儿子,说道:“先侯在日,甚爱成师,经常想废长立幼,只不过没有机会罢了,今君位既缺,我的意见,是想立成师为君。”一时议而未决,迁延之间,反被穆侯之弟殇叔拥兵自立,布告群臣道:“兄终弟及,殷商有例,同为献侯血脉,我难道做不得晋侯吗?”群臣不服,离去大半。殇叔恐世子兄弟起事,派兵搜捕,那成师素来孝悌,与世子友善,见情况紧急,对世子说道:“我兄可速往唐城旧都避难,来兵弟自抵挡,若能脱身,再去唐城与兄相会。”世子来不及多说,率亲随从后门逃往唐城不提。
再说成师,率徒众紧闭宫门,登宫墙拒殇叔之兵,对宫外来兵说道:“先侯弃世,尸骨未寒,殇叔擅立,你们追随不道,已是大错,为什么还要如此苦苦相逼呢?”来兵都低头不语,虽然也发动攻城,却都不甚卖力。对峙至夜半,成师约摸世子已经到达唐城,对群僚说道:“我军兵少,难敌逆叔,不如赴唐城会合我兄,徐图社稷。”群僚皆无异言,于是乘夜撤军,到唐城来会世子,兄弟见面,相拥而泣。
晋国群臣,听说世子在旧都存身,纷纷来投。世子见众心归附,于是和大家商议道:“殇叔篡位,窃据神器,仇兄弟二人远窜国都,未敢一日忘归国也,怎奈殇叔已僭立四载,急切间未可图。”话音未落,一人出班奏道:“殇叔逆天而行,以庶犯嫡,私篡大位,国人多不服,臣有一计,可灭殇叔,助主公归就大位。”世子见其人出言甚壮,急视之,乃是成师的师傅栾宾(晋栾氏之祖),急忙问道:“卿有何计?”栾宾回答说:“近日周宣王方崩,殇叔必然要斋戒设灵遥祭,不能视朝,臣请潜入翼都,暗暗结交城内忠义之士,主公可约期发兵围翼都,臣为内应,则翼都可破,殇叔可擒也。”世子大喜,扭头对成师说道:“若借先侯之灵,得除大逆,复国为君,当与吾弟共享富贵。”决定依计而行。
至朔日夜,月黑无光,世子依约发兵来到翼都城下,果见城内钟磬悠扬,并无戒备,世子一声令下,众军踊跃登城,那守军仓促受敌,匆忙应战。栾宾率领徒众,在城内绕城大叫:“世子已率大军入城,投降者免死。”守军疑惧,无心死战,霎时被世子突破东门,杀进宫来,殇叔逃跑不及,死于乱军之中。群臣拥立世子姬仇即位,这就是晋文侯,时公元前781年事也。
文侯即位,深感其弟成师患难之谊,又念栾宾复国之谋,于是善待成师及其部众,位在众臣之上,多居重要官职。晋文侯十一年,前770年,犬戎大闹镐京,杀死周幽王,文侯接到国丈申侯勤王密书,遂令成师监国,自己亲率甲乘来救镐京,会合卫武公、秦襄公、郑世子掘突及申侯,大破犬戎,将其驱逐出周境,迎立周朝废太子、申侯的外孙宜臼即王位,这就是周平王。平王升殿,封赏众诸侯勤王之功,特赐晋文侯秬鬯(音巨唱,香酒)、圭瓒(音赞,玉石),以及彤弓一张,彤箭百枝,虎贲三百人,授以征讨大权。平王又作《文侯之命》,歌颂文侯勤王之功,勉励他像文王时期的先贤姜尚、散宜生、南宫括、武吉等一样勤于王事,继承唐叔虞等祖辈功德,治国利民。文侯再拜受命道:“姬仇敢不应命,今后唯王所使。”晋文侯从此取得参与周政、辅佐天子的大权。
平王得到卫、郑、秦、晋诸侯的拥戴,得为周天子,因见镐京残破,地近犬戎,遂决意迁都成周,百姓扶老携幼,都愿相从,郑、卫两军,顺路护卫,秦、晋两军,因备犬戎来犯,不敢久留,各归本国。
再说虢公翰立,其父亲虢石父为周幽王的卿士,原是废掉太子宜臼的主谋,后来与周幽王同时死于犬戎之难,虢翰立将此杀父之仇记在申侯账上,并恨及其外孙宜臼。现在见宜臼即了王位,心中不服,说道:“宜臼无仁无德,为先王所废,民望不归,岂可再登大位?”于是寻得周幽王一个名叫余臣的幼子在虢地携(今陕西扶风)登王位,史称携王,出现了一周二王分居东西,分庭抗礼、共同号令天下的局面。平王虽然忿恼,怎奈迁都未久,国力空虚,加之畏惧虢国强盛,不得不隐忍十年之久。
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平王政权巩固,见时机成熟,于是就以太宰阳父为监军,命晋、秦两国往讨携王,两国受命,各起大军会于西歧之地,见了太宰,议定秦军在西,牵制虢军,晋军在东,往攻携城。单说晋文侯领命,同了太宰,来到携城,虢翰立见晋军来伐,一面遣人回国搬兵前来助战,一面拥着携王,出城迎战,立于兵车之上,扬鞭言道:“周天子在此,外臣为何不来跪见?”晋文侯亦在车上对曰:“我只知道洛邑有个周天子,不知道它处还有天子。”翰立怒道:“北鄙小国,怎敢以下犯上,我必擒你。”催车来战,晋军接战,两军混战于一处。翰立见援兵迟迟不到,心中很是着急,再遣人往催,方知虢军为秦军所阻,无法来援。翰立惊道:“本国兵不到,如何敌得晋军过,不如往归虢都,合兵一处,再作道理。”于是下令撤军西向。文侯乘势挥军掩杀,翰立军大乱,竟不及护卫携王,被晋军赶上,乱刀砍死。翰立退回虢都,闭门死守,太宰与文侯商量说:“虢国的先祖乃是文王之弟,辈高名重,不可苦逼,今逆王已诛,大功已成,可归报周天子。”文侯说道:“全凭太宰处置。”
周平王见除了心腹之患,闻报喜不自胜,说道:“晋文侯克慎明德,再显忠义,朕心甚慰,确实值得嘉勉。”遂将黄河以西原周地邠(音宾,今陕西彬县)赐于晋国,册封晋文侯为侯伯(一方诸侯之首领)。
晋文侯诛灭携王,结束了十年来二王并立的分裂局面,周室归一,消除了周天子的心腹之患,时人谓之“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称其功堪比周公,晋国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得到大幅提升,成为诸侯强国。
晋文侯三十五年,前746年,文侯病重,把弟弟成师和世子姬伯召至榻前,嘱咐说:“我的日子不多了。想当年殇叔篡国,我兄弟同心协力,共度艰难,幸亏祖宗庇佑,兄弟归国,得以继承君位。我死之后,还望你叔侄互相帮扶,如同我在世时一样。”叔侄二人含泪领命,不久之后,文侯辞世,群臣拥姬伯即位,是为昭侯。
欲知昭侯如何行事,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