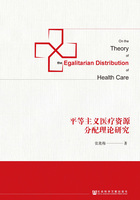
第3章 《导论》:医疗资源分配道德问题的缘起
人类的活动需要健康的身体,社会发展依赖健康的国民。当代医疗技术的进步拓宽了人类处理自身问题的领域,为伦理学提供了需要关注的新的问题。随着医疗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医疗服务从过去的照顾功能发展到治疗的功能,很多维护和延续人类健康的技术已经成熟,人们迫切需要这些技术维护身心健康,但是由于很多医疗技术费用昂贵,仅靠个人的力量无法承担,怎样分配医疗资源成为社会的一个难题,很多哲学家关注这个问题,其中平等主义理论尤为引人注意。平等主义是当代伦理学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尤其在分配正义领域影响更大,对医疗资源分配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平等主义理论。
医学对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医疗行为关系到人的生死,医学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和道德相关联。最初人类凭借本能抵抗疾病,通过互相帮助(抓挠、按摩、照顾)等缓解疾病的痛苦,还有另一种方法是求助于巫术,祈求神灵解除肉体的烦恼。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在进行医疗技术的探索,古代社会由于人类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准确的了解,医疗技术主要是从经验中总结得来的,这种探索往往是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如中国古代神农尝百草,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体解剖学的应用,医学从巫术、经验到成为科学直至临床医学的诞生,医疗对保持和恢复人类健康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医疗经验的探索还是治疗疾病的过程都体现了利他的道德因素。从古至今,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行医方式的改变,医疗领域的道德问题不断增加,人类关注医疗领域道德问题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
一 从医生职业道德到医学伦理学
古代社会主要关注行医者的道德,通过医生的道德自觉维护医疗行业的良好风气。古代社会医疗技术干预健康的手段非常有限,医疗作为技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是主要的方面,而医生的道德行为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成为主要的方面。医生主要是倾听者和帮助者,人们从医生那里获得了同情、安慰和帮助,这些行为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有时会对一些疾病有治疗作用,即使不能治愈疾病也让病人看到人性的光芒,感受到人生的终极意义,在面临疾病和死亡时有医生的陪伴和帮助会增强人对作为人的价值的信心。病人对医生的求助往往是一种安慰和同情的求助,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信任非常重要。这一时期医疗对人类的健康作用是有限的,仅发挥了关怀和照顾的功能,人们不关心医疗资源分配问题,因为医疗资源没有成为一种共同关注的利益,甚至很多人对积极的医疗持怀疑的态度,医生的主要工作是关怀病人,因此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医生生存的根本,如果医生道德品质不好就无法生存。在古代社会尽管存在固定的医疗机构,有最高权力机构对医疗行为进行规范,但是这些机构的医生是为上层社会服务的,民间多数医疗行为都是单个的医疗行为,如中国古代郎中和坐堂大夫行医,行医者与病人住在同一区域,双方容易相互信任,能够充分交流,尽管医疗技术落后但是双方关系非常亲密。医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如在中国古代社会,医师必须是仁者,医疗行为是行善的行为,“医乃仁术”,很多著名的医学家制定了规范医生的道德要求,如孙思邈在医学著作《备急千金要方》里专门有一篇论述医生道德的文本《论大医精诚》;在西方,古希腊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著有《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些典籍广为传颂,为行医者完善个人道德品质提供了规范。
平等主义医疗资源分配理论研究导论近代社会,医疗领域的道德问题扩展到医院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出现了系统研究医疗领域道德问题的学科——医学伦理学。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行医方式发生了变化,现代意义上的医院诞生了,医院按照工厂的流水线的工作方式为病人治疗疾病,医疗行为从过去的行医者个人行为发展为社会行为,医疗行为通过相互分工协作完成,行医者在医院作为一个群体和社会发生关系,不仅医院内部医务工作者的关系需要协调,医院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规范。这种分工导致病人不能直接体会到医生的关怀和照顾,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过去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变成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治愈取代关怀成为医生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在关注医生职业道德的同时,也关注医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医疗行为的社会效益。英国的医学家托马斯·帕茨瓦尔(Thomas Percival)对制定这些规范进行了探索,为曼彻斯特一家医院写了《医院及医疗职业行为关系方略》,1803年这个指导性文本出版,书名为《医学伦理学》,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从此医疗领域的道德问题不仅是医生的道德品质问题,还包括医院对社会的责任问题。帕茨瓦尔在当时已经受到道义论的影响,“用责任的社会契约分析,来论述个体与政府或官方的社会责任”[1]。医疗领域的道德问题不再仅仅是医生的职业道德问题,而涉及医疗职业群体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功利主义、道义论被应用到医疗领域,医学伦理学开始系统地展开对医疗领域道德问题的研究。
二 医疗资源分配问题凸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抗生素和磺胺类药物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医学逐渐成为科学,医疗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医疗技术真正发挥了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作用,人类具备了与疾病抗衡的能力。医疗技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现有的医疗资源已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由于医疗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制药公司、医院、医务工作者面临巨大的利益冲突,其是病人利益的代表,在医疗行为中获取自己的利益。由于医疗技术费用昂贵,医疗费用大幅攀升严重冲击了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怎样分配医疗资源才能让公民享受到有效的医疗服务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这个问题仅仅依靠医生良好的道德品质解决不了。当代社会人类对医疗领域关注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关注的主体从医生扩大到医疗资源分配制度,重点关注医疗技术如何平等地满足人类的医疗需要。
医学始终包含两个要素,一方面医疗技术通过师徒相传,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医学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认识,是一种世界观。医学从巫术、经验到科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医学既包括技术层面,这一层面用具体的医疗技术服务病人和社会,又包括人文层面,这一层面保证人们被照顾、被有尊严地对待,前者是医生应用医疗技术做的事情,后者涉及医生乃至整个社会行善的问题,如何行善需要伦理学的分析和探讨。因为医学的照顾功能需要全社会的协作,每个人都会面临生病、虚弱、死亡,不同的社会由于政权组织形式不同,怎样行善、怎样照顾病人的形式也会不同,“医学不仅仅与知识和实践、与治疗和护理有关,它还与权力紧密相连。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医学都涉及医生、病人的权利,以及像教会、慈善组织、保险公司、制药厂家尤其是政府这样的机构的权力或智能”[2]。医学从来没有和哲学分开过。医学解决如何照顾、治疗病人的问题,哲学家解决该不该照顾的问题。
医疗资源是卫生资源的一部分,是指医疗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医疗资源总是稀缺的,不能满足所有病人的需要,必须做出取舍。许多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医疗资源分配问题吸引伦理学家的注意。当代医学目的的转变使怎样平等分配医疗资源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医学目的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医学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延长寿命为宗旨,穷尽一切手段挽救人的生命。按照这个医学目的,拯救生命势必成为重中之重,所有的资源都会被用于医疗服务。当今世界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医疗危机”,快速发展的医疗技术导致医疗费用猛涨,即使是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被用于医疗保健,依然还有4000万人得不到基本的医疗照顾。“毫无尊严的生存却要消耗宝贵的社会医疗资源和有限的家庭资财,人类在死亡面前恋生恶死的巨大黑洞无法用技术与财富填充。”[3]由于人的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不加限制保证医疗资源的享有会成为无底洞,当今社会没有物质条件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病人的生命,传统的医学目的需要进行新的解读。
人的生命具有最高的价值,正如《黄帝内经》中的观点:“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病人的生命。传统医学目的的内核是尊重、保护人的生命,这一理念反对不平等的医疗制度,对病人一视同仁具有积极意义。医学目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医学目的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人类的技术水平的发展会发生变化。在古代社会,医疗技术手段简单,医疗费用不多,人类生存受天灾、战争威胁,也受瘟疫、饥饿等影响,寿命很短,不存在没有质量的生命还能活下来的可能。现代医疗技术可以使过去没法活下来的严重缺陷新生儿、脑死亡病人维持肉体的生命,这些人耗费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一些病情很轻、治疗后生命质量很高的病人却得不到治疗,不惜一切代价救治病人的要求已经不合时宜。美国学者丹尼尔·卡拉汉组织了来自21个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讨论医学目的,形成了一个报告——《医学的目的:确定新的优先战略》,提出现代医学目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照料那些不能治愈者,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亡。[4]人们依然希望自己的医疗需求能够被平等地对待,但是这种平等不是均等,是有差别的平等,人类的医疗需求随着医疗技术进步不断增长,而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病人的医疗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对不同情况的病人应该区别对待。这种平等到底是怎样的,迫切需要伦理学的分析讨论。
三 医学发展拯救了伦理学
启蒙运动后西方国家进入世俗社会,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关注效率问题,功利主义成为伦理学的主流,效率无可争议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伦理学家对效率问题的研究取代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经济学被称为显学,人们更多希望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于是伦理学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无的放矢,开始致力于元伦理问题的探讨,进行道德语言和逻辑的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但是元伦理问题不提供正确与错误的判断,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伦理学竟然没有任何办法批评,对正在发生的没有人性的战争视而不见,人们对伦理学失望透顶,哲学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伦理学越来越引人关注与医疗技术的发展不无关系,医学的发展拯救了伦理学,为伦理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带动了人们对伦理学的热情,人们希望伦理学解决医疗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最棘手的是医疗资源分配问题。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人们无限的医疗需求,医疗需求成为无底洞,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如何分配医疗资源摆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希望伦理学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如果伦理学家不能帮助解决医学伦理问题,他就应该闭嘴。仅按照效率原则不能解决医学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需要伦理学的解释与引导,医疗资源既要做到分配公平又要避免需求成为无底洞,耗尽社会资源,保证人类美好生活不仅需要医疗资源,还需要其他资源,如何达到这个平衡是个持续争论的话题,医疗资源分配问题成为伦理学家讨论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
伦理学理论对医疗资源分配问题有不同的解读。伦理学探讨人类行为的规范,人类行动包含三个要素:行动者(Agent)、行动(Action)和行动后果(Consequence)。伦理学理论对哪个要素最重要这一问题存在分歧,根据重视要素程度的不同分为三种伦理学理论,一种是关注行为的后果,被称为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一种是关注发出行为的主体,代表理论是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一种是关注行为遵循的原则,代表理论是道义论(Deontology)。这三种理论是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都关注医疗资源分配问题,但是关注的角度不同。
结果论基于结果的好坏判断决策正确与否,按照治疗取得的结果分配医疗资源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收益最大的人,但理论家对哪些是“好”的结果存在争议,需要对利益进行判断,由于价值观念的多元性,这种判断很难达成共识。在医学伦理学领域,效果就是治疗取得的内在利益,疾病的预防、治疗使人们免受不必要的病痛的折磨,改善残疾状况、提高生命质量、延长寿命被视为内在利益。结果论在医疗资源分配领域的代表是功利主义理论,功利主义理论按照治疗取得的效果分配医疗资源,按照其理论观点可以不给治疗效果差的病人提供资助。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麻省总医院的董事通过集体表决做出不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用于心脏移植手术的费用可以挽救很多病情较轻的病人的生命。功利主义的医疗资源分配政策显然没有平等地考虑每一个受影响的人。
义务论者反对根据效果做出分配的决策,根据义务论的理念,通过行为的结果判断行为的对错是错误的,义务论者认为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内在的本质,康德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康德认为人是理性的,这种理性的特征是人遵循的推断的准则普遍适用,道德源于理性而不是经验,义务源于推理。人类推理的这个规则就是“绝对命令”,“绝对命令”是普遍的法则,人们要无条件地遵守。按照义务论的理念,医务工作者的义务就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这个义务是无条件的、普遍的要求。医生对病人有治疗的义务,对病人要一视同仁,反对区别对待。
美德伦理关注行为人的品德,探讨怎样做个好人,怎样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与义务论不同,美德伦理认为责任来源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的规定,在医疗领域,美德伦理关心医生的道德品质,在医疗资源分配问题上与义务论不同,不依赖人的理性,而依赖经验,这些经验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智慧。美德伦理认为制定政策的人品德好自然就会制定合理的医疗资源分配政策,老祖宗留下来的做人的经验能指导医疗资源分配的实践。
医疗资源分配要考虑效果,也要考虑医务工作者的义务,还要重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品质,做出分配决策的人应该具有公平心。结果论、义务论与美德伦理都应该在医疗资源分配中发挥指导作用。